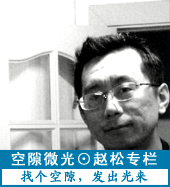一九九零年秋天,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坐在阳光满地的会议室里,等领导把师傅们带来……而现在,我眯起眼睛,像当时那样,试着看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明亮光斑,似乎它们就是记忆的起点和终点。师傅们是一些看上去懒散而又不耐烦的家伙。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不安而兴奋的青年跟以往的那些并无区别。领导讲话时他们不得不严肃而沉默地坐在那里,偶尔看看我们中的某一个。我有些紧张,这是习惯使然,更多的时间里是低着头看着漆面斑驳的地板上明亮的水迹,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拖地板,拖布水淋淋的,这就是一天工作的开始?徒弟们一个个地被师傅带走了。领导要求徒弟们要把师傅的本事挤到自己手里。而我感觉我们这帮刚离开学校的小孩很像等待被领养的孤儿。本来是一位眼神有光的师傅令我颇有好感,然而最后来到我面前的,却是另外一个人。我跟着他,穿过陈旧狭长的走廊,下楼转到外面柏油马路上,阳光下是师傅们带着自己的徒弟回休息室的场景。我走在他的身旁,有些局促。他随口问起我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声音柔软而平淡,他步履散漫,我悄悄打量着他腰上挎着的那套工具,显然是用的时间久了,才那么陈旧而光滑,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在了后面。
他是他们中看上去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工作服很干净,眼神温和,头发没梳理好,不过也不算潦草。我的失望无疑与他左脸那块胎记样的东西(暗红色的、有点类似于我们吃过的那种薄薄的猪肉脯,形状有些不规则)有关,也与他的温和态度有关,那时我们总是喜欢厉害的人,会在潜意识里轻视温和之辈。那一天到处都是阳光,即使是阴影都像青色明净的玻璃一样舒服。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这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师傅。在巨大的休息室里(是一套废弃装置所在的五层楼建筑的顶层、整个休息室空间实际上有六米多高),看了看外面那些沐浴着日光的银亮圆柱体装置之后,坐在那些大小不一的金属箱子旁边的铁条椅上,他都跟我聊了些什么呢?我几乎没怎么听他说话,而是尽量地在适应他的脸。其实,那是良性的血管瘤,年轻时被蒸汽击伤的后果,治过几次都不见效,只好死了心。之前,有个同学私下里告诉我,这个师傅是这里技术最不好的。这又无形中让我多了些失望,听着他讲这说那的,这失望丝毫也没有减弱。从他的眼神,以及语气的变化里,我能感觉得到,他似乎对我的情绪是有所觉察的。师傅不过是个名份,要是你觉得别的师傅好,也不是不可以跟他们的。他并没有这么说,这是我猜的。
他是个宽容的人。师傅们喜欢拿他的脸开玩笑,他并不在意。对什么事他都能一笑了之。他喜欢点评别人,比如Z师傅技术在整个厂里是最好的,但人很浮躁、喜欢耍小聪明;H师傅修电器的功夫很少有人可比,但为人孤僻、少言寡语。然后他认为自己的技术不如他们,但比他们有文化(有专业技术中专文凭),只是因为性格直率,说活不注意,得罪了领导,错过了机会,所以对于那些所谓的技术也就不在意了。后果虽然是涨工资几年都轮不上他,可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最重要的就是,他私下里告诉我,你自己要觉得好。他喜欢下象棋、看闲书、抽烟。他愿意这样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不过你不能学我,他说,在我这里,你能学的,就是不去计较那些没意思的小事,你就好好看书吧,技术学点就得,学的再好也没出息。也正是他的这段话,感动了我。也使我成了我们那拨同学里最不务正业的人。他们跟着师傅到车间里的时候,我则常常一个人呆在休息室里看书,或者躺在铁条椅上睡觉、晒太阳。那座外人很少留意的五层建筑无异于一个世外桃园。师傅总是说没事,你看你的书,有事我再叫你。除非人手不够,否则他是不会叫我的。那时也确实没人会跟我们计较这些事,那是个变化缓慢的几乎可以有田园牧歌的时代。同事们觉得我跟师傅般配得无可救药。
他的理想就是某一天能把他女儿送到爱尔兰过去读书,他有个外甥在那边打工留学。他愿意放弃安稳的工作跟过去刷盘子洗碗。外甥的妈妈,也就是他姐姐,是个有钱人。除了我,他从不对别人讲这些。他喜欢看那些关于政治秘闻或者奇人异事的书。这可以让他在众人面前吸着烟侃侃而谈。在谈的过程中他能获得很多乐趣和自信。那时候他会吸很多烟,每一口都吸得很深,仿佛这烟可以调动那些累积于腹中的故事。他喜欢重复这样的一种观点:所有的人都跟猴子似的,都有个红通通的屁股,扒开裤子是一样的,名人的屁股红得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厉害。这时候其他师傅就会嘲笑他是嫉妒心理使然。有人会很不屑地说,老百姓嘛,管好自己的屁股就得了。他就会极力辩论,举出一些例证,甚至说出一些单位领导的丑事。于是有人就会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提醒他道:你呢,这辈子没别的缺点,就是反动,外加嘴巴没门。他昂起头反驳道,反动了又怎么样,谁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人就会说,是啊,没人能把你怎么样的。说到这个份上,话题也就结束了,大家会很默契地不再接他的话头,顾左右而言其它。留下他自己呆在那里不尴不尬的,没台阶可下来。在他们眼里,他始终是个一事无成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有时可怜,有时让人厌烦。
我是逐渐开始喜欢这个师傅的。在我参加工作之前的那么些年里,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宽容地善待我。他的那个铁箱里摆满了很多书,他喜欢的,我几乎都不怎么喜欢,而我喜欢的他又几乎从来不看。他不怎么喜欢回家。每天下班后,都呆在休息室里找人下棋,或者抽烟看闲书。老婆打来电话催他回去,他会不高兴。他下棋几乎没有对手,时间长了人家就都不愿跟他下了。他就有些怅然。有时甚至不得不有意输几盘。他赢了棋不是什么新鲜事,输了棋才是大家都开心的事。每次下棋的时候,他的对手一方总会聚集很多人帮忙支招,难得赢下他两盘,就皆大欢喜地取笑他。有时候他输了棋会很不舒服,但随后就释然了,会自嘲一下。下棋么,他告诉我,也就是图一乐儿,太认真了没意思。后来有人找来个年轻高手,跟他下了十番棋,说是不为别的,就是要赢他这张嘴。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输了,输的很彻底,几乎没有赢的机会。从那以后,他就只字不提下棋的事了。棋瘾犯了的时候,就看棋谱。无论别人怎么引诱他,他也不为所动,自称水平不够。我们经常在一起呆到很晚,他愿意听我讲讲刚读过的书,只是他时常走神。我们有时喜欢一起站在窗口看外面寂静的厂区夜晚,那些装置上亮起很多小灯,星星点点的,而天空与地面则都是黑暗。他时不时的会弄出一包好烟或者好茶叶与我分享,都是他姐姐送给他的。
他的老婆是个很神经质的女人。这是他的说法。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质。是脾气不好?他摇摇头,说没那么简单的。他老婆很热情地端茶递烟,然后又做了饭。她有些歉意地表示,论做菜,还是你师傅在行。他的女儿是个很安静的小姑娘,总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长着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不远处悄悄看人。我看到一个和睦的家庭。后来他送我出来,对我说,家庭就是这样的,别人,从表面上永远看不出什么。我不明白他要说什么。有一回我路过他家,在晚上,看到他家灯亮着,就去看他。刚进到屋子里,我就意识到来的不是时候。他老婆在哭,满面泪痕,头发凌乱。他满脸怒气,什么也不说。他的女儿的房间门关着。我离开了。第二天他解释说他的女人很不懂事,被他教训了,涉及到的是老人的事。这件事过了挺长时间才通过他老婆的口说了出来。他说了谎。原来是他一直在跟一个女人通信。她在收拾库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争吵。他打了她。她说他指着自己的脸告诉她,如果没有这张破脸,他是不会跟她在一起的。她对我说这些事的时候,他也在旁边,麻木而沉痛。
她很爱他。他觉得无所谓爱不爱。自从这张脸变成这样,他对我说,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块斑,就是我的命。这辈子也就样了。那个与他通信的女人,是他在另一个城市读中专时不在同班的同学,曾经是个很秀气的姑娘。她并不认为他的脸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临毕业前他去拜访了她的父母,他们觉得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但他的脸相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们都不能接受。上火车之前,她在入站口对他说,我们保持通信吧。这通信,断断续续保持了二十多年。他说她最近得了一种病,头发都掉光了,丈夫也离开了她。他请了假坐火车跑去看望她。在医院里,她嘱咐他,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吧。过了一段时间,他老婆告诉我,你师傅学好了。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不抽烟了,也不看书了,每天按时上班回家,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他开始发胖,肚子也起来了。后来,也就是我做他徒弟的第三年春天,我调到了机关工作。他非常高兴。单位里的同事们给我送行,他喝了很多酒。最后在马路上,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师傅我,确实不象个师傅的样儿,什么都没教给你……。我说你一直在鼓励我看书,对我很宽容。他很难过地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其实人活着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么?我说我知道的师傅。不能光看书的你知道么?我说我知道的师傅。说完,他转身就走了,那感觉就仿佛我马上就要上炮火纷飞的战场,而他则要去当战俘。一转眼就是十来年过去了,他提前退了休,他女儿做了发型师,师母则是失业在家了。对了,我离开他之前,他特意送了我一套书作为纪念,四十卷本的马恩全集,几乎就是新的,没怎么读过。据说是一位领导退休前丢在仓库里的,被他捡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