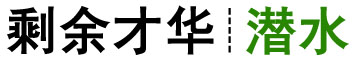I
(草皮从两栋根本不搭调的楼体夹角处开始隆起。身后的一栋是四层,左侧的是六层,分别在图纸上成为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从正常的呼吸中摆脱出来,鼻孔和口腔分别扯进一大口气,在气管处汇集,下沉到两肺,胸腔像填充了两个氧气瓶或者面粉袋那样鼓胀起来,越过隆起处已经看不到下腹部。最后一口迈过牙齿的气体留在了现在已呈哑铃状凸起的口腔里。水温适度的洗脸水在脸盆里慢悠悠地扭曲顶部的节能灯泡。把脸沉入水中。水溢出来一些。鼻尖能够贴到察觉不出质地的搪瓷脸盆底部,一堆花朵中间,没有放水的时候隐约能够辨别出藏于其间的人脸(花神?)。水珠,连成线或独立地砸湿了脚面,温热的水。被脸盆限定了形状的水像一块没化开的猪膀胱那样在做往复振荡。脸盆太浅,水只能浸到耳垂一点,原本垂在脑门上的头发现在浮在表面。两肺间的氧一点点在细胞中转化为二氧化碳。两腮依然鼓出,存住的这口气保证了水中的最后几秒。心中算计着秒针一格一格往前蹦,同时吝啬地放出几个泡。胸腔间的气自信地向上提,战线向前推移,很快,就剩下口腔堡垒。气泡成串的流出来,像不小心洒了的玻璃弹球,从口袋里蹦出来。咕咕隆隆。(完成第一个隆起的草皮向前滑开几米后,遇到极易被夜色抹去的一股小浪。左侧的楼在高处有几个窗口透出光,被夜雾托着不能掉下来。隔开草坪望过去与楼相对的是一排梧桐树,几盏路灯夹杂在掌形的叶子间,也太远,桔红的光递不过草坪来。经过这几股小浪草皮就安分地向前去,时常能看出背后的四层小楼叠印在草皮及我的影子上的浅影。月亮大概升起来了。)像扯一团棉花那样扯下一口气,塞在肺里,合上嘴巴。有大概半秒的停顿,扎下去。水溢出一块,哐地摔在脚下。眼球似乎能随着水的震荡在眼皮后面动,前几次在有肥皂沫的水中睁开眼睛,看见盆底模糊成一片的色块儿,眼睛酸得不行。新闻联播的主题曲荡起来,对面屋里父亲看报纸听电视,母亲坐在一旁打毛线。颇有控制力地吐出一连串的泡,听不见电视的声了,咕咕嘟嘟噜噜。当初他们用三轮把彩电运回来,牌子是夏普的,捣腾天线,兴奋地调出八个台,竟能收到转足球比赛的中央5台。有过靠在电视柜边举着固定在一个底座中的天线盯住不时清晰一下的电视剧看的经历。抬起头,(哗),水珠顺着脖子连接了小腹,憋住的那口气魔术般的转换成了陈旧的二氧化碳。(草皮,快要到水泥路的时候是那两棵泡桐。借助斜过来的路灯光,能看见染了桔红色轮廓绕在泡桐根部的螺旋状吐丝子。树根周围暗过草丛的一圈影子大概是泡桐的钟状花。远处隐约还能望见两栋楼形成的死角,好像所有的影子都从那里来。前面灯火通明的一处是小报告厅。)这一片平房蛮横得没有来历。沿雨毡向上爬过一段小坡度,屋顶就隆起来一块(鼓胀的肺),双手扒住瓦片,蹬脚把目光递过去望,是一片望不到头的房顶。看不见的空隙处不失时机地插着电线杆,沿电线传过来歌曲声,时下的流行歌曲,我闻到了消毒水味。大人们在午睡,歌曲声空荡荡地在四壁来回撞,贴着水面拉过来一条挂彩球的线分为了浅水区和深水区。(光泄到了分作三级的台阶上,在最低一级处滚做一个球悬在边沿下不来上不去。我踏上台阶。一个劲儿向下沉的男低音铺在两脚间,走上右侧的通道,拐过去绕进正厅,前面已经站上了几个人。和审判席一般高的最后一排听众的黑色头顶挂在身边耸起的栏杆上,避开先前站在那里的几个人,我这才看见坐满了报告厅的听众和前边像是因为听众席这种有意的倾斜而被挤在一根话筒后面的主讲人。两侧各有一个放在铁架上的音箱,大团的男低音通过电线压缩,到了音箱得到释放,像是游泳池中造浪用的涡轮机。灯光太亮,我注意到了自己脚边的泥,有意的并了并脚。“我们临终关怀医院于1995年成立,迄今共有85位老人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有人飞快地在灯光映得白惨惨的便条纸上记下笔记。)光着的脚丫在水泥地上留下湿印,鼻孔里翻腾着消毒水味,浑身的骨骼都有些过于兴奋的试图打开自己,以便一会儿在水中施展浮力。抓住太阳烤得有些熨热的铁梯,一级一级蹬上去,最高处传来中午时听到过的歌曲……忘记了站在上面看一看,着急的钻进一个管道状的滑梯里去,屁股下的水流根本不能将人在塑料制的管道中冲起来,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把自己往下挪,中间有一段太过平缓的通道则是干脆蹲起来跑下去的,就在见到出口的一瞬间又收回半躺下的姿势,准备将自己平着扔进水中,最好能像打水漂儿的石子那样在水上蹦两下。就在这会儿,从我背后冲下来一个胖子,和我一并摔进水中。到处是泡沫,就像磁带忽然卡住了,再也没有歌曲声(妹妹你坐船头),但是和《动物世界》里跟随鲸鱼的镜头中传来的声响差不多,一种更深的似乎是由肌肉中发出的声响,伏在四周。(关于临终关怀医院的报告作完了。我第一个退出来,摆在入口处的一块木板上海报的一角掀了起来,上面挂着迟迟不肯落下的小水珠。路面上积了一处处的小水洼,每个都储存了不少(也不多)的红色灯光。空气从远处涌过来,混杂了一些闷的汗液味,在小报告厅的门口凝固住,加上后面即将喷涌的人流声,都逼迫着我趟破几个小水坑快走几步。扭开门把,看到里间同时用作暗室和书房的小房间,漆黑一片,窗帘早拉得死死的。)
II
他们打算真正让我开始学游泳了。有教练,有伙伴,但是没有救生圈。他们把一个塑料泡沫系在我背后,打算让我相信就靠这么一个小方块我就能在深水池中立于不沉之地。我不喜欢这样,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在自家的脸盆里练习憋气,虽然我明白这样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征服海洋,但总比让一个全身仅被一条小裤衩兜住的陌生男人来摆弄我的四肢强。表现很差,或者非常偶然我的同伴恰巧全都比我强,他们一个个真的像小海豚那样在水里蹦来蹦去,不停地在教练周围比着溅起更大的水花,用他们新学到的划水动作在教练的带领下离我远去。越游越远,在这个小泳池里他们就准备好了日后要横渡大西洋、太平洋或者印度洋。我也试着摆弄了两下新的划水动作,可是我的下半身始终在一个劲儿作对似的往下沉,只有我的两只像在求救的手能在水面以上拨弄出动静,而这根本无法把我带离岸边。幸好背后系的塑料泡沫还在,它并不全是一个谎言。依靠它我可以像被吊在空中那样吊在水面上。脸冲下的时候我验证了自己憋气的能力,不再像在家里那样闭住眼睛而是在水的张力的帮助下把它睁得足够大。池底一条条绸缎般的反光从我的左眼晃到右眼,左眼晃到右眼,我的肚皮成了最好的救生衣,把我稳稳地贴住在水表面,四肢不受控制地打算离我而去并荡过我的身体,它们会像四根香肠那样渐渐聚拢到岸边,然后被教练发现并打捞上来,他们会忙着寻找香肠的主人,急得团团转。一股一股的水波漫过我的耳朵往耳朵眼里灌,先是左耳,再是右耳,水波正犹豫不决到底将我推向哪一边,左边,右边……后来我学会把泡沫挪到自己的胸前,试一试面对新的局面。我的两腿不再像划水时那样陷在水里,它们大方地浮上水面,我稍稍仰起头便能观察到我红润的脚趾的情况,水波依然依次问候我的两个耳朵。我闭起眼睛,在眼睑后面安心度过两个小时。此时我的伙伴都将塑料泡沫交给我看管,自己则奋不顾身地在已经显得不够大的泳池里举行世界冠军童年里的第一场游泳比赛。我只要偶尔关心一下堆在岸上遭到废弃的塑料泡沫就行,并且发誓和我背上的这一个仍在继续使用的永不分离。我无法意识到我是否失去了什么别的孩子正在享用的乐趣。尽管有时候一个人像个死尸那样漂在离岸边最远不超过我两个胳膊的地方确实会显得有些无聊,但我再也不想看见当教练试图从我背后取下塑料泡沫并把我就那样扔在池中央的时候因为我奋力反抗而在他胸前、两臂抓出的道道红痕。他们都习惯了我的不存在,就像我已经习惯了将游泳池当成澡堂。有一天,我的眼睛湿了。那会儿我正像往常一样躺在水面上。突出在水面上的鼻尖跟着也湿了,我看到雨点前仆后继地向我砸过来。下雨了。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们在哪里,但是我不能离开这儿,不是因为岸上的塑料泡沫,我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雨点砸在那堆塑料泡沫上发出“扑扑”的闷声,不断有人上岸,池水完全被搅乱了。这时我决定到水底去,我要潜水。我先是弯了下膝盖(倒好像要跳出去),接着收紧腹部,头向水底探,不行,完全被水挤出来了。这会儿我才想起背后的泡沫,解下它,扔上岸,用手扒住伸入水中的梯子,吃掉一大团空气存进全身凡是有能力装下它的管道中,接着用手把自己一级级往下运。水没过耳朵的一瞬间,所有的嘈杂声都消失了。转而身处一个炮火密集的战场,我鼓动两眼向上看去,有无数的水泡在上面炸开,隆隆的轰炸声几乎要把我在水中挤爆了。但是水下不再有任何人,我逐渐撑过了不知多少分钟,直到水终于在我全身的毛孔中自由进出,而远在头顶的雨无法接触到我的一丝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