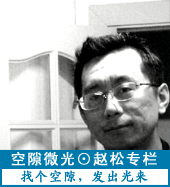胸怀浪漫的人在现实主义的环境里会轻易就成为异类。而做异类总归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无法被量化,很多时候,它不但不会体现出什么触目惊心的东西,反而还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莫可名状的寂静里。这寂静并非缘自他自我的保护与封闭,而是由他人创造的,它能让一个具体的人在群体里永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尽管你意志坚强,胸怀宽阔,随时都可以自我调侃,就像轻蔑地谈及那些委琐之辈一样,然而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大家通用的游戏规则里找到某个靠边的位置,不再有个性张扬与反动,可是你仍旧不能真正地被环境所接纳同时又无法避免环境本身对你的腐蚀,不是心灵的,就是肉体的。从处于惯性状态的日常生活氛围中的群体角度来看,任何浪漫的个体都是天真而又奇怪的不合时宜的存在。在成人的世界里,天真常常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说在这个世界里贪婪与残忍都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么天真则永远是不能被理解的,它不是被漠视,就是被嘲弄。
我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浪漫而天真的人。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你兴冲冲地打电话到班组休息室找我,可我不在,你让我师傅转告我一声,次日下午去厂报编辑部找你。我去了,可是没能见到你。不知是由于太阳离地面太近了,还是因为内心兴奋而又忐忑不安,我一直有种睁不开眼睛、不知所措的感觉,我给你投过一篇改过二十几遍的稿子,我已经没有力量再去修改它了,把它投入信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坠入了某个并不危险却又陌生难测的深渊里,不能逃脱也不能落底。在你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那期报纸的校样,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的字,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我的文章旁边有一篇你专门为我的文章写的评论,比我的文章还要长一些。坐在编辑部的沙发里,看着阳光透过窗子倾斜着在地板上留下一块有些变形的方形光斑,我的头脑里只有异常明亮的空白和异常脆弱敏感的空白,而视线所到之处又都是那么的美妙而宁静,包括墨水的气息、散乱在地上的报纸,还有那几盆矫揉造作的盆景和植物。
有些场景我想不清楚了,比如,我们的第一面是在编辑部里,还是在通讯员培训班上?我只是清楚地记住了那期通讯员培训班原本并没有我的名额,是你临时找领导争取的。这在当时的年轻人眼中,是一种类似于荣誉的东西,因为入选者不仅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坐在教室里听厂报的编辑们讲写作常识,还能被带到海边的渡假村里吃海鲜、联欢、看日出、在沙滩上漫步。过度的兴奋为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做出可笑的举动,我在你讲课的时候,写了一个纸条,意思是说,如果我将来成为作家,一定不会忘了你。下课时我把它递给了你,然后掉头就走开了。我们二十几个年轻人一道去了兴城。你却因为家里临时有事,没有去成。对于那张纸条,你没有任何反应。此后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你从没有提到过这张纸条的事。在海边,人们几次提到你的那篇评论文章,还有我的那篇散文,只言片语都足以令我兴奋不已,实际上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怪人发现了另一个怪人。我拘谨,腼腆,不善言辞,手里握了本袁宏道的尺牍选集,跟在大家的后面,有种略显尴尬的沉默。有张照片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当时的心境,看日出的时候,我侧着身体,把衣领竖了起来,初春的海风还很冷,我尽可能地缩着脖子,表情疲惫,皱着眉头,眯缝着有些茫然的眼睛,而左侧眼镜片的后面,则是一点朱红的朝阳,自然弯曲的头发被潮湿的海风吹得越发的粘软了,有几绺搭在了额头上。
随后,在回去的火车上,我又做了件令人惊讶而又显得夸张的事,就是蹲在地上,把座位当成桌子,一口气写完了我的第二篇散文作品《海·日出》。在文章的最后,我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抑地把日出称之为黑暗的海奉献给我们这些过客的伟大诗篇,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诗。在我写的过程中,不时有人伸出头来看看我。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举动实在有些夸张。但是我当时确实多少体会到了一些写作的畅快。这个新闻很快就传到了你那里。在你的办公室里,你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完全能想象得出当时的场景,我的样子,以及大家的反应。你笑的时候,眼睛会自然眯起来,牙齿整齐而漂亮,声音略带些鼻音,很富有弹性,有点像合唱团的领唱。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时在火车上他们一定觉得我非常可笑。你说不要管他们,笑就笑吧,你还是你就行了。而你呢,我逐渐知道了,你一向喜欢偶尔做些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或者不明白的事。他们不明白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画妆。也不明白为什么你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跟女同事们讲自己的生活琐事。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下班人潮涌动的时候偏偏要穿一身白绸旗袍招摇出厂。你当时的领导为了这些事,没少找你谈心,劝你不要再挑剔了,差不多就结婚吧;要多跟同事,尤其是女同事交流,不要独来独往;在上班下班的时候尽量不要穿奇装异服什么的。你平静地反问领导说,首先,旗袍是国服,为什么不可以在上下班时穿呢?其次,我有男朋友,我只是不想展览他,也不想早早就结婚;而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们,实际上永远都是什么都说不明白的。领导很失望地看了看你,提醒你不要过于骄傲、目中无人了。你微笑着摇摇头,不会的。
管你叫廖素,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W的,那个喜欢张爱玲的女孩,我们曾经一起去过你家里。她的文章比我的好。她很有天赋,而我没有,我只有勤奋。她之所以叫你廖素,是因为你素面朝天,从来不施粉黛。也是因为你心地善良、坦诚待人。W去美国之后,还在E-mail里问你的情况,那时我已经到了上海。她跟那个捷克裔美国工程师生了两个女儿,经常跟着他到世界各地去,偶尔会写些随笔,但并不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看书和教育女儿上。在那张她跟两个女儿的合影里,她看上去健康而饱满,与在抚顺时完全不一样,而她的文字也变得平和冲淡了。她让我转告你,你最后跟她说的那些话,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谢谢你,她爱你。我把这些话转达给你的时候,你的眼圈有些发红,声音也有些发涩和颤动,你不得不放慢说话的速度,你们曾经发生过争吵,很长时间不再说话,令你异常痛苦,后来,她重新来到了你的面前,却是告诉你她要离开的消息。这一次,她爱了一个喜欢沉默的捷克男人。她跟你一样,在厂里制造了一次新闻。你看,你所关心的,都是跟你差不多的在言行上让别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怪人。
无论是天真还是善良,其实都不算什么问题,你最致命的弱点,是你容易怜悯。你甚至会怜悯你的敌人。在你的敌人受到不公正遭遇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客观地表达出你的看法,为其辩护。在别人眼里,包括被你怜悯的人眼里,这种行为无疑是可笑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从不会怜悯任何人。他们只喜欢嘲笑别人,他们也喜欢憎恨和诅咒。在不懂怜悯为何物的环境里,其实你注定要一直孤立下去,还要背上名为“愚蠢无脑”的光圈。因为你会本能地怜悯,他们觉得你是那种怎么对你都可以的人,既可以随时谈笑风生,也可以随时把你弃之于污水沟。那个经常拼酒的女人不就是这么对你的么?可是在她醉倒撒泼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去帮她一下,因为在她的空虚浮躁情绪里,你又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怜悯。
这几年来,你与世无争,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你缓慢地写作。与以前的那种强壮的身体状态相比,你现在的身体真可谓麻烦不断。腰间盘脱出令你吃尽了苦头。还有些别的问题。你差不多都已经习惯了。我们见面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每次回来,见到你,最后总是忍不住要问你,是不是还在写?听到你说还在,心里就觉得很欣慰。我还记得你的一篇散文的开头部分,写的是你的想象与梦境的结合,渐行渐远的一个人,凌波而去,从长白山的余脉,进入到远古森林的深处……那时候,在我看来这只是你的一时想象而已,并非你的本性所向,你是个满怀热情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永远都不大可能转身就离去,做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即便是你对身处的环境无比厌倦的时候,你也是带着不服输的心理混合了厌倦的情绪努力支撑着。你永远都学不会与人争夺什么,更是学不会与别人斗法玩头脑,搞微妙的人际关系,你真正学会了的,只有沉默。
这次国庆节回来,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状态。后来就打听朋友,才知道你已离开了宣传部,被调到了远离总厂的西区,做驻站宣传员。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你躲进某间偏僻安静的办公室里,每天准时上班和下班,除了写稿子以外,就是看看书,或者不声不响地出神,透过窗玻璃,看着不远处林立的炼油装置和储油罐。大多数时间里,你都是那种非常难得的独处状态。这一次,是你自己申请去那边的么?要是遇到了你,我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我倒是希望是。实际上,我希望是由你自己来完成这次转身而去的。在那个环境里浸泡多年,你也该到彻底想通的时候了。
2006年10月2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