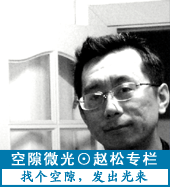他的右手,食指跟中指都是僵直的。它们不能像其它手指那样灵活运动,甚至不能做简单的弯曲。它们就那么僵硬地伸直在那里,要是抬起手,它们就会指着什么地方,这里或那里,垂下去的话,就不声不响地指着地。如果从一生的角度来看,它们刚好就相当于生命的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他这个人的缩影,既是对其个性的概括,也是对未来的某种预示。它们继续坚定地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固执而无用,等于什么都没有占据。然而任何时候他出现在你面前,你都难以无视它们的存在,即使是他的整个手都在发抖,它们看上去也仍旧保持着那种倔强而又旁若无人的状态。
在我还在读中学时候,我曾问过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的母亲,高昆的手怎么会那样?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有些含糊其辞,她好像不大想让我知道什么似的。后来我只好直接去问高昆了。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低头用拇指跟无名指熟练地捻碎旱烟叶,均匀地把它们洒在左手拈着的弯成弧形的卷烟纸上,然后转动它,卷成一枝头大尾小的旱烟,掐去纸尖,叨在嘴里点燃,烟头冒出一小团火焰,随后又变成了一股浓浓的白烟。他的回答简单明了,在机修厂里上班时被机器挤了一下,就成了这样。对这个答案,我很怀疑,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过了两年,忍不住又去问他。他想都没想就给了我另一个答案:摔的,翻墙的时候,右手撑到了地,弄伤了这两根指头。说完还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明白了,要是过些时间我再去问他,答案估计会变,说不定会是打仗时被击伤的,也可能说是冬天里伸到外面冻坏的……。他也知道我不信,就有些勉强地笑了笑说。看来你比我还关心它们啊。后来我大了,终于知道了它们之为它们的原因。那时他差不多也老了,思维迟钝,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了。
母亲的那些学生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早,也最为深刻。他从上中学开始就经常没事到我们家里来玩。我六岁那年的除夕,一家人正在包饺子,他跟一个同学带着满身寒气进来,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过了没多久,很多人在我们家院子外面敲门,大声叫嚷着。我们紧张地跟着父母出去,开了门,只见外面密密压压地站了几十个精壮小伙子,手里都拿着木棍铁锹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手电筒,向我们晃来照去。母亲什么学生都教过,什么顽劣的弟子都修理过,上百个学生斗殴的场面也见识过,所以就显得镇定自若。她心平气和地问他们,“你们是哪的,干什么,来抄家么?”那些人里,有几个很快就认出了她,“这不是韩老师么?您家在这儿啊!我们的灯笼被人偷了,跑到这边来了,那我们就不打搅您了,就当先给您拜个年吧。”手电筒的光从我们这里移开了。母亲也看出了说话的人是什么人,“哦,是你们啊。”随后,一群人乱糟糟地唿哨而去了。临走他们还不忘大声向别的地方丢下狠话:小子哎,听清楚了,别让我们抓着你们,抓着了,打断你们的腿,当灯笼挂树上……
后来高昆跟那个同学又溜了回来。我母亲道,“是你们两个小子干的好事吧?”高昆得意地撇了撇嘴,歪了歪头。北河后街的那帮人,一向是以好勇斗狠闻名的。他讲起刚才的惊险场面,他们跑到北树林那边去撒尿,那群追出来的家伙也到了那里,没等他们把裤子提起来,就给人堵住了。“他们问我们从哪过来的?我们说从东城。‘有没有看到两个拿着灯笼的家伙?’我说我们刚过来时,碰见两个人提了两个大灯笼从炭素厂旁边钻到胡同里去了。那帮人就放我们走了。”想着他们在树林里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上的场景,我既觉得惊险,又觉得好笑,就特别愿意挨着他。放完鞭炮,吃饺子的时候,高昆低声告诉我,那帮人里有个人曾经跟他打过架的,还挨过他一棒子,“竟然没认出我来,嘿嘿。”其实啊,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这个高昆,虽然看上去眼光凶,其实是个很稳的人,心里没谱的事是不会做的。
那时他还没留起小胡子,脸部线条很清楚,有股锋利的感觉。平时话不多,喜欢戴个半新不旧但洗得干净的军帽。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他常出没的几条街上,不少人都隐约有些怕他,怕他的眼睛,那双单眼皮下面透露出的光线有时会忽然变得很冷,远远的。那年代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事没事打架斗殴是常有的。在三十中学的那些年,高昆其实没打过几次架,但每次打得都很出彩,因为对手都是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且名声在外的家伙。他从不打群架,每次都是单挑。他学过武术,很会打架,出手是又准又狠。被他打败的那些人,没有恨他的,都很服气。有一回,跟他单挑过的两个小子被一大群邻街的小子追打,经过他家门口,眼见着就跑不掉了,正在门口的高昆拦住了那些人。“差不多就行了,”他抽着烟,拎了一块砖头,站在路中央,面无表情口气平和地对他们说道。那些人有点意外,你谁啊?“我高昆。”那些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他把烟掐了,很随便地蹲在地上,一边用那块砖头慢慢地敲着地面的冰,一边半抬着头,斜着眼睛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给他的这种作派镇住了。其中的一个领头的,打量了他一会儿,说我今天就给你个面子,高昆是吧,记住你了,有空到南马路这边玩,找我,我叫李春。
这个李春,就是后来一把铁锹砍翻了六七个人,警察围追了一整天才抓住他,后来被重判了十年。他弟弟叫李秋,是个瘸子,脚筋被人挑断过,整天拄着根拐杖,可仍旧是个出了名的狠角。高昆跟他们兄弟喝过两次酒,聊得也可以,但始终没混到一起去。李春生前对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高昆,你呢,跟谁也混不到一块儿去。他不知道高昆不混在那种人里,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他老爸,老爷子是当兵的出身,脾气暴烈,他对我母亲保证过,老师你放心,高昆敢迈错哪条腿,我就打断他哪条腿。二是因为我母亲,她对高昆说过,你小子要是混到那种人里,就别说是我学生。三是因为一个女生,跟高昆是同班同学,名叫陈什么敏,长得很清秀,我母亲说她有点像林黛玉,平时不喜欢说话,是个冷美人。高昆一直很迷恋她。她也挺喜欢高昆的。他们不声不响地恋到九年级毕业的时候,高昆把她带回了家,让父母看。母亲觉得这姑娘面相不好,是苦相,会克夫败家,颧骨高,眼光冷清。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父亲没表态。陈姑娘什么都没说,就跟高昆分手了。她知道高昆是个孝子,不想因为自己让他背个不孝的名。后来,她跟了一个比他们高几届的男人,再后来呢,她没结婚就怀孕流了产,还住了院,而那个男人却不管她了。当时不少人都拿她当作笑谈,可高昆不管这些,径直去医院里照顾她。
这事被人们一传,就变了味道,高昆成了事主。而那个丢下陈姑娘的男人,倒成了受害者。生活作风的事,当时对于任何正派人家来说都是门面的事。高昆的父母觉得颜面扫地。他父亲拿着棒子就去医院清理门户。见到高昆别的没说,一棒子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高昆下意识地抬手一挡,棒子打在他张开的手上,打折了那两根手指。高昆什么都没说,就是那么默默地看着父亲的眼睛,垂着受伤的手。他父亲极力要挣脱劝架人的一堆手,可是挣不脱,只能怒目而视,骂他是畜牲。据说当时他们父子两个就这么对视僵持了十多分钟。陈姑娘把被子蒙在头上,不声不响地哭了。……后来,到了冬天里,数九寒天的时候,高昆结婚了。对方是他父亲老战友的女儿,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开朗的姑娘。而那个陈姑娘,则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城市,嫁给了一个部队连级干部,做了随军家属。她在我的印象比较模糊,只是个隐隐约约的一个形象,皮肤白净,眼睛安静而明亮,没有声音。
高昆的理想,是做个车工。中学毕业后,他顶了他父亲的班,进了机修厂。右手坏了,他就练左手,把它练得跟右手一样灵活。我父亲那时也是车工。他看过高昆干活,是这样评价的,“悟性好,胆大心细,手法利落。”手艺固然是好的,但在为人上,他跟他的那两根手指头一样不灵活,尤其不懂怎么跟领导相处,再加上平时惯于独来独往,不苟言笑,把自己弄成了边缘人。而且他的脾气变得大不如前,发作起来比他父亲还火爆。若是惹火了他,就算是领导,他也照骂不误。也正因如此吧,后来企业改制,他是车间里第一个被通知买断回家的。买断之后,他的脾气更差了。整天哪都不去,就闷在家里。他的妻子倒是个乐天派,虽说没什么文化,却是个对什么事都看得开的人,任凭高昆那张冷脸如何阴晴圆缺,她都不往心里去。用她的话说是,你不理他,他过了那个劲头,也就那么样了。不过,后来高昆开始酗酒的时候,她撑不住了,就来找我母亲,让她出面说说高昆。
我母亲很了解高昆,见到他以后,也没劝他,只是聊起以前在学校时的事。聊着聊着,自然就聊到了那些往日的同学现在怎么样了。随后就聊到了那位陈姑娘。前些时,母亲在沈阳遇到了她,现在过的挺好的,跟她男人转业到了地方,找了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人也白白胖胖的,生了个男孩,都九岁了。“她还问起了你,问你过得怎么样。我说你也过得不错,就是脾气不怎么好。她说你是个孝子,是个讲义气的人,可就是不懂得心疼自己,还说要是赶上好环境,你应该能有点出息的,因为你很聪明……”话没说完,高昆的眼圈已经慢慢地红了,什么也没说,起身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脾气也好了些,平时除了安心做自己的事,就是跟妻子、女儿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在喝酒这件事上,始终都没有改。他原本就是个酒量大的人,每天晚上要是不喝上半斤白酒,连饭都吃不下去。酒精的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那只灵活的左手,就是喝酒废掉的。他得了手抖的毛病,发作起来,有时候拿着钥匙连门锁都插不进去。这样一来,想再继续做车工也做不成了。
转眼有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把高昆这个人忘了。所以前年春节回家,初三那天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有些意外。他一个人拎着两瓶酒和一些熟食到我们家来拜年,顺便跟我父亲喝酒。他的变化之大,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个人都老了很多,头发留得长长的,干枯而凌乱,而且在脑袋后面扎了个小辫子,胡子有点像老山羊的,脸庞瘦削露骨,眼睛看上去也暗淡无光,眼角还有很多细长的皱纹。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胖了。”我说你可是瘦多了。“我老了,”他的右手还是那样,中指跟食指伸得直直的,微微有些不自然的颤抖,指着地面;左手端着酒杯,也在轻轻地抖着。我有点没想到的是,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如今,他在自家附近的街角开了个配钥匙的小店,生意不温不火的,但也足以维持生计。母亲担心我多问什么不该问的话,就示意我不要再说了。他呢,也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喝完了酒,然后就走了,神情有些沮丧。但在临出门的时候,还是冲我努力笑了笑,“你真的是长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我也笑道,我都三十多岁了啊。
他走之后,母亲跟我慢慢说起他的一些事。他的妻子一直在跟人合伙做煤炭生意,去年认识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男人,一来二去的,不知怎么的就好上了,一起去了趟广州之后,回来就跟高昆提出离婚。高昆呢,也没说什么,离就离吧。他也确实是没喜欢过她。他现在是自己带着女儿过呢。他女儿正在读高二,学习成绩不好,性格也是古怪不驯,整天跟一帮不着调的孩子混在一起。他也懒得去管她,觉得这孩子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从性格到容貌,一点都不像他,也不像她母亲。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这也不是愁的事,人各有命吧。谁都管不了谁的。”他父亲前年得了中风,在家里瘫了一年多,又在家里挨了半年,去年冬天死的,死前一直都是高昆在照顾他。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