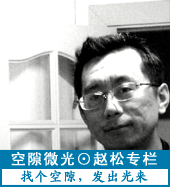想起来,那时你穿着裤脚肥阔的大红裤子,从那些待客的出租车后面跑过来,在那个冬天里的上午,来到这个灰色冰冷的广场中央,摆动的裤脚遮住了厚底鞋的边缘,几乎就要被地面的灰尘沾染了……模糊不清的阳光在云层后面难以透露出来,有些蒸汽似的雾从对面大厦后方一阵阵浮上空中,静止片刻,然后很快地就散了去。你跑过来时的动作是那么的奇怪而又可爱,你的步伐并不快,只是有些夸张,每一步都不像似在跑,而是在降落,小腿朝两侧摆动,有些笨拙地带动了红裤腿,像尾翼似的减缓了降落的速度,从远处,也是从半空中,你忽然的就降落到他的眼前,刚用冷水洗过不久的脸被冷风吹得发红,而头发匆匆梳理过,还是湿的,在脑后扎了两根不长的马尾辫,暗红泛金的发丝都有着波浪式的弯曲,看上去乱糟糟的……你停在那里,控制着急促的呼吸,侧着头,抿着饱满的嘴唇,略微眯缝了一下眼睛,看着他。无需凝固,那些气息就此再也不会散去了,就在那里始终停留着,如同空气,它就在那里,你也知道的。想想看,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多少有了些传奇的效果呢?这个过程所构成的瞬间里,还可以继续分解下去,更为细致地分解成无数的细节,在他的记忆里,还有想象里,尽管是转瞬即逝的,可最终仍旧是凝固的结晶体。
你朋友的父亲,那个据说通易学的人,怎么会想到这个名字呢?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个名字在他眼里都是那么的自然而单纯,似乎与现实世界全无瓜葛,而更近似于某种泄漏天机的方式。它看上去真的就像个梦,或者是与之相关的水晶球,天然的钥匙,无意间带给了他,可以打开隐秘之门。出乎你的意料,他从这个名字里读出了那个本来的名字,那个在古代意味着智慧的、看上去姿态孤单而寂寞的字,支撑着它的是眼睛。他把你当成了那种能预卜未来的人。而你呢,有他想的那么神秘而复杂么?无论如何,他都显得太过遥远了,就像野海上空偶然出现的一只不知来自何处的信天翁,本应跟随着某支远行船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自个呆在那里,像个关于风暴的信号。那时你还没有把服装店开在那所学校的后街上,还没想到“狂奔的蜗牛”,你跟丁子去某个北方滨海小城里度假了,天阴着,不宜出行,只能呆在房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你告诉他,你们住的地方靠近一个很大的工厂,灰尘漫天,不远处是墨绿的海水,时不时地把脏东西和灰突突的沫子推到海滩上,不可能游泳的,没有金黄的沙滩,只有棱角尖锐的青黑石头漫布在那里。漫长的海岸线上几乎看不到人影。海面是寂静而荒凉的,你称之为野海。
当时他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城市里,也在海边,是个港口,离你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晚上,体型庞大的重型货车像怪物似的不断从泥泞的道路上涌到港口外面,一些探照灯般的强光从高处打到港口里,货场以及附近的海水被照耀得如同发着奇异光芒的来自另一世界的出土文物。他站在巨型油轮的前甲板上,俯身看着下面的海水在白光下动荡,要是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就能看到水里有很多细小的鱼,它们似乎就是以轮船上丢下的食物为生,随便有什么小东西坠入水中,它们就会聚集在其周围,不停地啄食。就这样,湿漉漉的海风不断吹拂过来,透入外套和衬衣里,冰凉得有些发涩的肌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泛起一层细小的疙瘩。他只是来这里透口气的,同事们在酒店里继续喝酒,吃各种生猛海鲜,酒力不胜的他早早就躲了出来,随即就发现眼下的这个城市在进入夜晚之后几乎就像个空城,街旁的店铺不到八点钟已统统关了门,马路上不但看不到行人,连车辆都很稀少。穿过那个大得惊人的广场,他觉得自己走进了坚硬的水泥沙漠,那么大的广场上只有不多的几盏地灯是亮着的,那时他想到了你,几经周折……
那时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渴望用纳博科夫那种充满灵感的方式以舌尖的细小动作来分解一个名字,他只是出于近乎本能地感觉到了那种绝望而又安静的感觉。在他想来,绝望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啊。就像里面发霉的浆果随着牙齿的轻微压力不经意就在嘴里爆裂了,那种令人沮丧的气息就开始向空间里弥漫。它们是乏味无聊的工作,家庭的矛盾纠缠,难以理喻的人们,污浊的空气,汽车带起的灰尘、排出的尾气,是路边大排档烧烤羊肉串发出的浓郁火爆的焦香肉味儿,有时也会是丢在床下时间过久的半瓶没了二氧化碳的汽水……。你是希望么?你姓氏名谁,家住何方,做什么的,是男还是女,他什么都没敢多问,就像美梦中人,生怕自己多问一句这梦就会醒了。那个虚拟世界里的虚拟名字似乎具备了所有神秘的能力。他是后来才想到用舌尖来细细品味这个名字的,若……对,不管他如何放慢舌尖下落的速度,那名字听起来怎么都像似一声轻轻的叹喟。那时他身边还没有人听他说到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它,以及它后面的你。没有形象。整个名字与声音,都被他转化成了一个幻念般的发光物体,留在雾气蒙蒙的窗玻璃上面,留在闪烁的背景里……巨大的一轮明月在道路的尽头静止着,银色的清冷液体漫过道路两旁大树的枝叶上面,你们还在路上,长途汽车就像一只八眼怪兽闷声叫着奔跑在黑夜里,高速公路两侧沉寂的农田被焚烧残禾的浓烟所笼罩。你们不声不响地透过窗玻璃,看着外面黑暗的原野怎样被月光浸染得明亮起来。
关于你的信息,太有限了,最基本的线索都不能构成。他的时间慢慢地发生了混乱,不管在哪里,他的脑子里时不时地会忽然浮现猫叫声,还有那些你惯用的词句。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他并不知道你那时没什么事可做。除了你,还有你的那些“老婆们”。你有好几个老婆,据说都是前世七百多年前在元朝时结的缘,那时候你可不是一个安静而神秘的姑娘,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倍受皇恩的中原巨富,娶了很多女人,而他呢,则只是个终南山的道士,这些听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从一开始就是坚信不疑的,当然这也是后话了。他相信机缘,相信天意的暗示,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一本蓝色封面的薄书跟一副普通的手套所带来的温暖似乎抵御了全部的寒冷。它们暗示了什么呢?那本书丢在了出租车里,他告诉了你,第二天你就去省城的图书城里将它买来寄给了他。他不知道是你先去的书城,那书还剩两本。他拿的其实是最后一本。晚上,他遇到了那辆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把那本被水浸过的书还给了他。这样他就有了三本同样的书。这意味着什么呢?失而复得,还是三重可能变化的线索与方向?那本书是法国人艾什诺兹写的,名字是《我走了》。
显然他把你的某种天赋无限放大了。有时恍惚间觉得你是个精灵,走到哪里,随手点化,那些普通的东西就会焕发珍宝的光芒。在他的脑海里弥漫着光怪陆离的色彩之雾和波浪的时候,自然天气也忽然与他合上了拍,那天下午他从银行里出来,没精打采地骑着自行车,穿过狭窄的街道,这时候他并不知道此后会发生百年不遇的沙尘暴,沙尘与云层混杂在一起的厚度会达到十三公里,在下午三点多钟,天就黑得跟入夜一样,外面散落的是稀疏的雨点,每个雨点里都含有很多尘埃微粒,而在雨点的空隙里不断坠落的仍旧是沙尘颗粒,这些,怎么可能想象得到呢?他所能想象得到的,是那种世界末日般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虚无――从此以后,什么都不会有了。他把这初次见面当成了最后一面。要是当时有摄影师透过出租车窗拍下他的面孔,就会发现他当时的表情过于肃穆了,似乎他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事实:地狱跟天堂就像云层里的阴阳电核似的在尘世里汇合了。就是这些夸张的戏剧情绪引导着他,那种怪异的表情足以让你远远地就认出他来。要不是你主动走过去,他会像个被雨水淋透的木头人,呆在那里不知所措。你还能记起那一刻他的表情么?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后来,在灯光温暖而辉煌的肯德基里,你拿出十几张班德瑞的音乐CD给他,然后是没头没脑的对话。后来你们分别坐上出租车,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在一个十字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你们的车意外地并排停了下来,他看到了你的背影,而你却在看不远处雨中的那座陈旧简陋的火车站,它是白色的。
那个问题奇怪而简单:是?他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不是。通过了。谢天谢地。他拿到的是信箱密码,几封以前的信,你家的街道名称,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从这个固定电话里,后来他听到早晨窗外市场里传来的喧闹声音,还有你母亲的问话声,有些粗糙的声音,有时候也会是你的继父,听起来他们都老了。某个下午,他在办事途中转到了那条街上,天色暗淡,他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七层的楼房有很多,他仰着头观察那些窗户,想知道从哪个窗户伸出头来才能看到下面的公共汽车站,还有那个便利商店,但是一无所获。他不知道的是只要再往前走上十几步,向左转,再左转,那幢楼就是你家所在之处了。如果从这里出去到市中心,并不需要走他来的那条街,而是要走前面的那座大桥,过了桥一直往前,再走二十分钟就是了。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条街,就是一个世界。他每次去那里,都要进街边的小商店里买包香烟,每次买的都是不同牌子的,然后抽着烟,坐上公共汽车离开这里,穿着整个城市,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那些不同牌子的香烟就堆在他电脑桌的边上,很长时间都没有抽完。
河堤路上靠近河岸那侧护墙上的球状装饰灯被人敲碎了很多只,里面的灯泡被拿掉了,剩下的那些只有很远处看起来才是明亮的一串灯,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你们经过那里时,每盏灯的间距都在不断增加。从这座桥走到西面的另一座大桥,需要一个多小时,过了桥再经过体育馆,走过山脚下的那条安静的马路,穿过那些陈旧的红砖小楼,一直到你的家里,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他奇怪的是那时冬天的夜晚竟然不冷。每个月里都会有两个夜晚属于这条漫长的散步之路,不停地走着。不是一起向前,是面对面的走着。这道路的距离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回到各自的世界里之后你们会通电话,很长时间,有时会说到天光微明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僵掉了,透过窗玻璃上没有霜花的地方,可以看见大理石般静寂冷清而又平滑微明的天空,然后是远处幽暗的山脉。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庞,放下听筒,两只轮换使用的耳朵差不多都失去了知觉。在其它的时间里,你们通信。
“王阳明《传习录》有一则游南镇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天亮时,我拉上布满郁金香的窗帘,屏幕上出现最后一行暗黄色的文字……躺在细竹凉席上,闭上眼睛,给自己留下一个黑暗的地方,面对着墙,听外面各种声音随着光亮出现。过去的几个小时,漫长的梦,每一句话,每一段沉默……睡过整个上午,外面到处是热烈的光,我回忆一切细节。上街,世界依然如故,我已有所不同。看着世相,耳朵里却响着梦幻般的声音。词语。晚上我看到了树,在黑白的世界里,一缕暖流通过叶子和枝静静流向深埋土中的根。”这是最早的信了。你在回信谈的是什么呢?他手里早就没有它们了,只有你还有。他只有残篇。“这三天过得真是不易。若是没有电话,你周围的人就会把你淹没,在你的声音出现的那一刻,我能看到你的头发、脸庞从人海波澜凌乱变幻中浮现,那么短促。在这里,除了到阳台上张望,什么都不能做,而远处有的是些破旧楼房、脏乱的街道、无精打采的人,破碎的纸片、塑料袋飘扬在空中,五月里日光混乱,室内阴暗。我试着在心里重建一个地方,说话,吃东西,散步,或者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呆着。这几天,一直头疼。没有事可做。白天,晚上,某个时间里,你在做什么,想什么,是什么样的,光线是从哪个角度落到脸上……”而你的回复,则始终是那种电报体的文字:“我习惯了/习惯早早就听到你的声音/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你让我习惯/可是/今天/你哪里去了?/你的声音/你的人/我感觉不到你的气息/……/今天去了医院/人真脆弱/我很怕/去的时候就不停的抖/真的没用。”
“我不知道声音的世界会这样的奇妙,同我一向沉湎的文字世界是如此不同,黑暗降临、没有他人的时候,声音使世界浑然如一,你就在这里,转眼就能看到你,既使一动不动地背向着你也会清晰地感觉到你。我不知道幸福的感觉会如此浓烈地出现在声音里。时间不存在,那段声音里除了幸福什么都没有。在声音里我们挨着,眺望窗外那条黑暗的马路、远处华灯下的大街、往来的车辆、空寂的楼宇、偶然亮起的灯光、远处的树林、还有暗淡的山脉。这些是一,完全的一,无彼无此,无远无近,在声音编织的阿拉伯飞毯上,漫游天地之间,无所羁缚。如果不是青色的堆着暗淡积云的时间浮现,我真以为漫游会永无终了,正如你所说的,会在醒来后发现容颜已老青丝成白发。它把现实空间再一次放在我们中间。外面逐渐亮起的那一切,正在响起的那些无关的声响,没有什么能为这刚刚过去的幸福作一下点缀,声音还在耳边重复,越来越远,很多人来了。如此惶惶然,幸福之后,是一无所有,不知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工作中抬起头来,呼吸一下,看一眼外面,那个声音的世界忽又浮现了,你的声音,气息,依然如故,我恍然醒悟了:既然我已知道你在何处,你是谁,那么就永远不会失去了。”
他知道文字是另外的事。它们不能代替那些琐碎的场景,一点都不能。说个故事吧。“从前有个人,他有个梦。一天他去海边。沙滩是白色的。海水是绿色的。他赤足走着,后来停下来,在光滑结实湿润的沙滩上,用脚趾头写字,后来就用手指来写。他随心所及地去写,启初只是单个的文字,后来是简单的短句。他看到远处灰色的海鸟一动不动地呆在岩石上,而别的大些的不知名的海鸟则在天空中无声滑行。他仍旧是安静的。直到那个女子在无意中经过这里时,他已经海滩上写了很多字迹,和他平时在纸写的不大一样了。她问他,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他说写写字。她一边读,一边笑着说,很有意思,你的字让我想到别的东西。他想了想,说你怎么会来这里?她回答说是因为没什么事,以前也常到这里透透风,今天刚好经过这附近,就过来看一看。她说道,不过我想的是,我来这里之前,我来之后,都一样。是你的想法在不停地改变。深绿的海水缓慢地失去了光泽,天晚了,太阳也落了下去,海滩上只剩下那些奇怪的文字,它们正在经历着被消磨消灭的过程,先是在字划里充分地蓄满冷清的海水,然后厚厚的海浪反复地来到这里,不动声色地使海滩恢复本来的面目。”这个故事其实最初讲的时候,被他演绎得有些伤感,现在放在这里,我拿去了一些过敏而又容易给人以造作印象的词句,如果现在由他再来重述一遍的话,则他一定会觉得很陌生。而你当时看着屏幕上这一行行似乎早就存在的文字不断浮上来,是不是隐约觉得此人真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奇怪的家伙?透过只言片语能感知到某种无法分析的东西么?
你是安静的,然而这安静也只不过是你的外壳。你是温暖的,虽然你自认这温暖并不多,却也足以温暖他的生活了。他有他的欲望与幻灭,而你有你的哲学――如果不能向前,那么还不如倒退,退下去,甚至退到很远处,就可以重新向前走了。其实一切早已预演过。所谓的结束可以通过你把手从他手里慢慢抽回来完成。离开长途汽车狭窄空间,你们站在傍晚的街边,呼吸着凛冽寒气,他语无伦次地问着。没有为什么。只是一瞬间。第二天早晨,他昏昏沉沉地坐上出租车,一路上经过的,刚好就是他跟你经常走过的地方,在白天里,在这样的心境下,那些原本普通的景物――路边的灰白积雪,冰封的河面,以及河面上黑乎乎的冒着热气的洞,还有河对岸山脉上的雪,转眼都成了盐。一年的最后一天。他跟朋友坐在冷清的房间里,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结束就是结束。没有什么能把结束变成延续。他有种天灵盖被突然打开的感觉,脑子里一阵冰冷,那些能产生记忆与思维并指导行动的东西全都暴露在冬天里了,所有的细胞都结了冰。然而,就像幸福变成痛苦只是抽回手的事一样,痛苦变成幸福,只是一个电话的事。你用了另外一种形式,看起来就像你用纸巾擦掉他嘴唇上的油渍一样简单而温柔。他觉得你就是上天派来引导他走出阴影的人。你从来都是那样安静地侧着脸看着他,就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出现,然后带他离开。他感觉到了,可是没有真的懂得。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结束只能自己到来。就像死亡那样。不可预期,也无法回避。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好奇心,就足以毁了整个世界。你再也飞不动了。你收拢羽翼,在地上低着头安静地走路。你需要安静稳定的日常生活。不需要任何奇迹。你向后退去。这个世界上没有精灵也一样可以继续下去。即使不通任何占卜之术也一样可以继续下去。没有答案是对的。他去了南方,而你去了北京,继续你的服装生意,还有了婚姻。在南方,最初的一个月,他沉陷在回忆里。弱不禁风。后来他不去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与场景了,而是去回忆那些令他沮丧、恼火、嫉妒的场景,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象到的。他希望它们就像缀在笔端的墨水一样,能把那些文字般的记忆全部抹黑。他想起后来你开始准备离开时的样子,没有声音和表情,还有一个谎言……那时他没有想到你已离开了。他想到你在那人的办公室里帮着接听电话,处理些杂事……那时有很多时段都是空白的,任凭他如何胡思乱想都无法添补内容……你在商场里散步,你说一个人,而他就在商场外面,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等着你走出来,不是你,是你们,那人伸出手臂搂着你的脖子,而你们的表情看上去都有些郁闷,你心不在焉,但也还是自然的。有些个晚上你会忽然的就消失了。他会突然打车跑到那座桥上,或者你家楼下的暗影里,希望能看到你,哪怕看到的是你们,也是好的,他与其说是在等着你,等一个人,不如说是在向你归还永远都还不清的什么。任何反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你们在步行街上散漫地走着,并不知道他就在后面不远处跟随着,他最后忍不住把电话打给你,因为他看你并不是快乐的样子,拿起电话,你就哭了,他也跟着哭了,还有那个人,在你身边的人,也跟着哭了,奇怪的场景,三人同悲、不知何为。就这样,他觉得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在南方的大城里把自己安顿下来,想念与你相关的人与事,景与物,想念丁子,甚至还有你丈夫、你未来的孩子,他觉得自己能像爱你一样爱上他们。这种无可救药的感情完全错了位。他竟然爱你们,而不只是你。这也是倒退,他如法炮制。
对于他来说,回忆并不会带来慰藉,但有可能使内心生活延续下去。想到了与你有关的什么事,或者是忽然遇到了与你相似的人,他会跟孩子似的突然兴奋起来。确实有这样的人。无论是肤色、脸庞、嘴唇还是牙齿,还有神情与举止,都与你非常相似。这种相似有些令他不安而恐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子,也告诉了别的人,每一次描述,似乎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重新确信一次,这是真的,而不是幻觉。谁能说不是幻觉呢?去年冬天里从那座商场你的专卖店里经过时,他不就是与你面对面地只有一步的距离,而并没有马上看出是你么?那时你的形象是出乎意料地缓慢地唤醒他的记忆的。刚从睡眠中被惊醒的丁子过了好半天才进入他的语境里。她声音懒散,那边在下雪,天气倒并不冷,昨晚她基本上没怎么睡,现在整个人都有种漂浮在水上的感觉。她似乎并不想与他探讨那人与你像或不像的话题。她后来想了想,告诉他,你现在过的很好,正在考虑能有个小孩,每天生意上的事也很顺利……。他听着,从大厦的底层屋檐下走了出去,外面还在下雨,毛绒绒的雨丝缓慢的飞舞着。他钻入出租车里,小声告诉司机地址,然后继续听着,她有些困倦了,她不清楚他为什么还会这样缠绕在过去的事里。他也不知道。他尽可能缓慢地解释自己的感受,出租车驶上了高架桥,外面流动的是光影与黑暗之物,他觉得自己随着出租车向上浮起又慢慢滑落,在这个湿漉漉的夜晚中划出了一道不明显的抛物线。是什么将自己这样随意地抛了出去然后又落了下来呢?他下了车,回到住处,坐电梯上去,开了楼道灯,有些犹豫地走到自己的门前,拿出钥匙,开了门,他说丁子,再见了,不打扰你了。然后关上房门,反锁了。他有点累了。躺下去却又没办法入睡,索性就坐起来,仔细地翻着床边那些书,它们堆在他的周围,要想找到一本适用于此时此刻的书,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最后他把手重新停在了那本前些时刚看完的书脊上,“漫漫长夜旅行”,塞利纳的。他记得塞利纳在那部书的扉页上杜撰了一首十八世纪法国王室瑞士卫队的队歌,他还给你读过:“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在严冬和黑夜之中,/我们寻找自己的路径,/在全无光亮的天空。”这段话,现在是不是只与这部书本身有关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觉得就应该把你的最近的一段话写在下面:永远不说,就是永远……。
200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