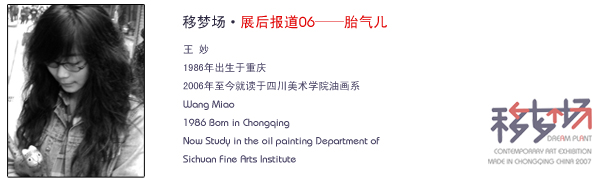
访谈
记者:展览结束后庆祝了没?好像其他几个参展的都睡觉去了。
王妙:我也去好好睡了一觉啊。太折腾了。
记者:什么最累,你觉得?
王妙:制作的过程。
记者:听说你的面粉发酵了……
王妙:是的。我的困难都在制作过程中突发了,什么情况都有,因为我的东西只能在现场做,有时间限制,而且工程大。
记者:有没有因此而觉得更刺激,更好玩?
王妙:太刺激了!之前有预感会遇到困难,但比我想象的要多,更突然,所以完成了之后,无比刺激。
记者:觉得完成得怎样?自己满意不?
王妙:满意。过程很重要啊。
记者:没错!
记者:准备过程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产生类似“我在做一件非常棒,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感觉?
王妙:一直都有,不论是之前,还是过程中。
记者:你觉得这种感觉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有多重要?这种“激情”之类的感觉。
王妙: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动力,更好玩,催化剂吧。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它。
记者:这算是一种年轻的特质吗?
王妙:不呀!任何年龄都有吧。
记者:可是年轻人身上好像更突出一些呀。这个展览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也包含着这种气质?
王妙:是哦。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整个展览都有这种气质。
记者:谈谈你的作品吧,最初的灵感来自什么?
王妙:胫骨睡在床上逼我想方案,他在被窝里,我坐在边上想了很多,他说都做不出来。我气得想拿被子憋死他(开玩笑的,我没有做啊),最后看了看他,慢慢联想啊,就来啦,哈哈。
记者:……他让你联想到什么啦?
王妙:不是,是当时的个人状态。
记者:说一说呢,怎么从当时个人的状态,联想到这个作品的?
王妙:觉得自己刚刚在进入另一种生活,时间在慢慢走,而我被一种孤独、迷茫、不能呼吸的状态凝固。空空的,透不过气。
记者:于是你就用面粉这种材料来表达这种凝固、让你不能呼吸的感觉?
王妙:嗯……是吧。
记者:电视机和沙发,是你心目中代表生活的符号吗?
王妙:是吧。一个生活空间,很普通的那种。
其实不简单,哈哈。
记者:啊?说一说说一说!
王妙:这种空间,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是种平常的生活,但是作品中没有人去演绎。我幻想着每个观看者都试想把自己也生在其中,觉得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有人光顾了那样的状态。
记者:你有邀请的态度在里面?邀请观看者进入你构造的空间?
王妙:是的,不过只是自己想象。别人进入过没有不知道,后来也没有去关心了。观看者大多都说:这个好乖。
记者:哈哈!自己觉得呢?
王妙:就像我在舞台上跳舞,观众说:“这妞够辣。”我对自己,作品,展览很满意了,足够了。
记者:原来还是不希望自己很乖呀……!
王妙:呵呵。
记者:你觉得用有形的形象去表达这些的个人感受,是艺术的意义所在吗?
王妙:艺术的意义我不懂,好玩吧。
记者:好玩很重要?
王妙:对我来说是,哈哈。而且这作品中有更多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就像有时候别人更清楚我自己。
记者:经常脑子里迷糊着?
王妙:哈哈,对。
记者:其他几个参展伙伴的作品看了吗?觉得怎样?喜欢谁的?
王妙:看啦,都很好啊。44、胫骨的吧,看起来很气势。
记者:什么叫气势嘛?!
王妙:呵呵……不知道……别逼我了……(一个冒冷汗的面团人)
记者:这是什么呀?那团发酵的面团吧?
王妙:是啊……
记者:我很好奇,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艺术家?
王妙:没有特别喜欢的(主要是不了解)……嗯,喜欢席勒,贾科梅第……
记者:07年有没有打算做什么作品?
王妙:胡乱想了一些方案,有机会就做出来啊。
记者:平日里你是不是喜欢胡思乱想?
王妙:是的,什么都想。
记者:比如呐?给我们描述一个。
王妙:一个房间上下左右都有透明的特强胶质,很厚很粘,很有弹性,我在里面玩跳跳。
王妙:就是出不去啊玩死我了。
记者:(笑惨了……)你会不会被粘在地板上啊?或者弹起来时候粘在天花板上下不来?
王妙:就是啊!哈哈哈哈哈。
记者:反正也是死了!
王妙:就是,不如玩玩。
记者:你觉得这样子死掉怎么样?
王妙:还好啊,就是想妈妈。
记者:好乖哟……
王妙:那是!
记者童末 发自南京
作品





作品简介
王妙
作品:《天塌了》 装置
材料:面浆,电视机,沙发
作品简介:把电视机和沙发(165cm×80cm)相对放,中间相距2.5米。电视插上电源,屏幕显示“雪花”(有声)。把面粉加水豁成浆状,把沙发和电视机覆盖(除电视显示屏),同时覆盖围绕电视机和沙发这一地面空间(4m×4m),成不规则形状,并且面浆在地面有3-5厘米。不规则厚度。
作品文案: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驳论。如果把天的倒塌当作一种暴力的威胁,那地面的平静安逸则可当作是对暴力的暴力化谋反。在这里,艺术品再不是作为陈述思维的载体,艺术已经沦为了众人都可以众说纷纭的口水本。所谓的语言的有限和无限可当作是对作品之内和之外的隐喻,那正好,你的天塌下来和我的天塌下来都不可能压倒权利和大众意识。个体经验已经被消解到只有靠大众审美的一点点卑微同情和好奇维系自身的命脉。我试图告诉自己,面浆、电视、沙发这些大众生存愉悦的物化思量完全可以引起我对宇宙的探索。你不信?我也不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