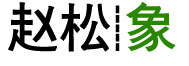“看到一个同伴死去很长时间了,胃已被土狼吃掉,或是只留下一地白骨,它们会紧张、狂躁。它们挤在一起,走向同伴的尸体,耳朵微微张开,抬起头。它们用鼻子接触整个尸体,像吸尘器一样嗅上面的气味,如果发现象牙,它们会用鼻子将其卷起到处走。”他读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下面的那些沉默的学生。要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其实是有些古怪的,似乎大象鼻子嗅的不是那些东西,而他们的手或者脚,紧张而又刺激。不过从他们的愚蠢的面部表情来看,实在是看不出任何智慧的光泽。他们只是好奇而已,不可能理解他的意图。“……在肯尼亚苏塞克斯国家公园,他们将大象的头骨、象牙、犀牛和水牛头骨,还有一些木头放到大象面前,除了其它大象的尸骨外,它们对死去的哺乳动物没什么兴趣。它们对象牙最感兴趣,会把有感觉的脚轻轻地放到象牙上面,小心地蹭来蹭去。有时候,活着的大象之间也会用鼻子彼此触摸象牙……1970年,一位动物学家在非洲密林深处看到了大象的葬礼的全过程。在离密林几十米处的一块草地上,几十头象围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雌象。当这头雌象倒在地上死去时,周围的象发出一阵哀号,为首的雌象用长长的象牙掘土,用鼻子卷起土朝死象身上投去,其他的象便一起这样做。一会儿,死象身上堆满了土、石块和枯草。接着,为首的雄象带领众象去踏这个土堆,直到它成了一座坚实的墓。众象围着墓转了几圈,像是在与遗体告别,然后就离去了。”
他把光盘放入光驱里,然后走到门边,关掉靠近讲台的那些灯管,只保留教室后面的那些继续亮着。等他不声不响地走到最后面,转过身的时候,前面的投影屏幕上已开始显现动物的世界。那个老播音员的低沉深情的声音,从两侧地角的音箱里夹杂着轻微劈啪声慢慢散布出来……外面在继续下着雨,教学楼的灯光漫延到四分之一操场时就已经暗淡许多,有几个孩子在低声说话。“它们,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在凌晨时就显得烦躁而不安,从树林后面就开始不断加快移动的速度了,黑夜在后退,它们仿佛被夜晚脱落下来的一大团黑暗,迅速移动着,队形显得有些过于紧密,然而它们似乎丝毫都不在意这样,彼此时不时地摩擦坚硬粗糙的身体,没有人能预料它们移动的确切方向……”孩子们都不再说话了,跟影子似的沉默在那变换闪动的投影屏幕的光亮里或者外面。他看了一眼旁边伏在桌面上的那个男孩。那孩子侧着脸,睁着眼睛,眼角的泪珠早已破裂干掉了,眼光暗淡地看着他右侧的墙壁,他觉得这双眼睛肯定也是看了他一下的,当然还不能确定,这种十三四岁的男孩,谁有把握能猜出他们什么时候是有感觉的什么时候是冷漠的呢?至少他做不到。不过他现在已没有刚才的那种厌恶情绪了,他看了一眼地上断掉的那根色泽暗淡乌亮的木教鞭,看上去有点像光滑的树枝,皮被剥掉了、在水里浸泡过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风干、反复在手里摩挲过。
它们对那群犀牛突然发起攻势的时候,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短促的惊叹,随即就陷入了沉默。他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喜欢他们的,这样想想的那个瞬间里,他感觉右手腕子隐约有些痛,这是用力过猛的后果,没错,他从来都不擅长发力,以至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在突然发力的时候轻易受伤,这样的,那样的,而多数的时间里,他还是习惯于尽可能让它们处在沉寂的状态,有时他甚至喜欢它们慢慢变得麻木起来,喜欢那种从神经末梢传来的微妙发麻的感觉,没什么规律的,就像超低伏的电流,时不时地在他的脑海里反射出那种不经意的波动,那些波纹会慢悠悠地重新返回到那些末梢。他有点疲倦,就是现在吧,他觉得自己的骨骼在皮肉里开始出现松散的征兆,随后浑身上下都有种陆续下坠的感觉。前面,黑白的景象里,它们,那些青年象们,已将那二十几头犀牛逐个杀死了,完全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杀戮。之前,在家里准备这一课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看过三次这个场景了,但还是隐约有种古怪的伤感情绪,从心里泛出几缕类似于潮湿木头或者腐败的树枝树叶燃烧后的烟味。他又看了看那个孩子,仍旧保持着刚才的那个姿势,耳朵上的那点血迹已经凝固了。他伸出左手,轻轻搭在那张看上去有些发僵而实际上很柔软的脸颊上面,那孩子没有任何动的意思,也没有表情,尽管他的手有些湿冷,搁在脸上会让人很不舒服。
早晨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儿子继续躺在被子里,蒙着头,说是头疼。这孩子向来就有这毛病,大概从五岁起就有了,每次家里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就会适时发作起来,程度有轻有重。不过今天看来没那么严重。儿子的表情基本上还是平静的,但他还是同意他不用去上学了。他抚摸了一下儿子的脸庞,现在感觉好些了吧?儿子闭上眼睛,轻轻地嗯了一声,就不再出声了。他看了一会儿之后,才穿上外套、背上文件包出了家门。出门前,他随手把厨房的灯关了,犹豫了一下,又回去把灯打开了。这种橙黄色的灯光带着些暖意,映亮了走廊地板上的一小块,这样看上去比较舒服,他知道,儿子跟他一样,不喜欢家里有人的时候一点亮光都没有。儿子十二岁了,刚好是地支的一轮,他想不起自己十二岁时的情景,只是隐约记得那时自己在读小学五年级或者初中一年级,是少有的一段安定的时光,所以才会没什么具体的印象。再往后一年,事情就记得比较清楚了,在另外一个大城市里过暑假,一个叔叔带着他玩,在家里看麦克哈里斯从大西洋海底来,呆在部队大院里的那套旧阁楼里,一个夏天都在那里,直到有一天叔叔的父母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家里没有事了,回去也该上学了。他们派司机开车送他回到家里,感觉比来的时候快得多,公路两侧的那些长满庄稼和野草的墨绿田野还有大叶杨树都来不及细看就过去了。他记着自己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而小叔叔坐在前面,斜对着他,侧歪着身子,摆弄着那个魔方,转来转去,偶尔会抬起眼睛看他一下,有时会笑一下,有时挤一下眼睛,似乎在提醒他什么彼此都知道的事。家里显得很干净,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让他一时有些不能适应,感觉像到了别人家里,陌生的人,他母亲正在做饭,而父亲则在院子里弄电视天线。新换了一个更高更结实的杆子,上面支的是铝制星形天线,确实是新的,那些扭出旋转波纹的铝条上面一点锈蚀痕迹都没有,而那些螺丝上面的机油也像昨天才注上去的。他在院子里转了转,熟悉了一下环境,看见厨房窗角下多出了一丛繁盛的深紫色的花簇,似乎还在从里往外钻着绽放。父亲回过头来,对他笑笑,以后能看到更多的频道了。
麦克哈里斯能在水里呼吸。这对于那时他来说,无疑是解决了一个心理难题,这个事例意味着人沉浸在水中即使很长时间也不会窒息而死,当然前提是要找到大西洋,这种可能才会得到验证。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至少有人做到了,沉浸水中与死并不是一对矛盾。这跟他后来成为生物老师有什么关系么?如果说有的话,可能就是那时埋下的根子,他想知道生物学角度下人的其它可能。当然,现在他作为一个生物老师已然清楚地知道了一个常识,人是不可能在水下长期沉浸的,因为这种水下呼吸功能并不存在,也无法培养,那些无氧下潜的时限与深度虽然一直有人在不断突破,但那只是努力而已,只是在不断地证明长时间沉浸的不可能。说到底,人不是两栖动物,只能在陆地上活着,然后死了。人是无知的,又故作什么都知道,用人的声音,表达动物的情感。比如那个低沉的声音说,“那些青年象都是孤儿,它们的父母之前被野生动物园的管理者们猎杀了,以保持这个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因为规定数量有限,它们不得不被以这种方式开除出去。人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和答案。然后,人们从外面找来一些成年大象,它们的出现不出意料地解决这里的危机,青年象们温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躁易怒了,不再乱冲乱撞了,也不会去攻击犀牛们了,它们的生活从此变得平静而温和。”荷尔蒙,孤独,以及外界的刺激,这是科学上的理由,就像那个男孩在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仍旧用双手紧紧卡住前桌同学的脖子,而他不得不用教鞭击打他的脖子和肩膀,直到教鞭断掉他的手松开为止。事件的原因,据那个被卡住脖子的同学只是说了一句他“长得像头臭大象”而已。
孩子们不大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些成年大象来了它们就变得温顺起来,它们并不是它们父母啊。他们发现,这是个假象。但显然他们还不知道一种形式上的稳定比现实的真正稳定要来得容易。他引导他们展开讨论。他提醒他们,我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了解动物的世界,动物们也不会理解我们怎么看它们。他留了作业。然后,他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重新走到后面的那个孩子身旁,把手伸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的手比刚才要温暖一些,而孩子的脸庞则比之前要凉一些,温度发生了转换,这样他的手就可以在那里多停留一会儿了。那孩子仍旧是没有任何反应,或者说没有任何回应的意思,但他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他眼光里流露出某种厌恶的意思,冷冰冰的一束微光,比玻璃碎片还要锋利一些,也更脆弱一些,他实在不忍心再去碰一下它们。后来,他问他要家长的电话号码,要家庭住址,那孩子都没理他。最后一节是自习课,他告诉那孩子课后不要走。说这话的时候,他没再去碰那孩子的脸,尽管他仍旧是安静地伏在桌面上,保持着与此前相同的姿势。他把那个被卡脖子的男孩带到了办公室。他很想知道这孩子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招来了那孩子的愤怒攻击。事情并不复杂,只是多了些细节,那个男孩整个下午都在踢这个孩子的椅子腿,一下一下的,后来他忍不住了,回过头去,对那孩子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长得跟该死的大象似的。其他同学都笑了起来,然后他的脖子就被那双瘦硬的手死死地卡住了。之前呢,他边听边问道,你说过些什么别的话没有?这个孩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对他说,暑假的时候,我爸爸要带我去美国,去迪斯尼,还有五大湖区……他就问我,怎么不带你去非洲呢?我说非洲是个野蛮的破烂地方,只有大象和土狼,还有黑人。他说你懂个屁啊。我说那你就让你爸爸带你去非洲好了,要不让你妈妈带你去也行。他就一直踢我的椅子。”
校长大人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里,神情严肃而有些忧郁地注视着他。这是他第几次打学生了?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有些尴尬。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学生家长投诉你,可你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吧?他注意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放着那两截断掉了的教鞭,它们本来被他丢到垃圾桶里了,不知道谁又这么细心地把它们捡了回来,放在了这里,作为证据。那个男孩没有投诉他。他下手也确实重了些,校长说那孩子的脖子和肩膀交界处有一道明显的淤血痕迹。另外,校长还告诉他,这个孩子的所有作业和考试里,你的生物课成绩是最好的。你明白么,这说明什么?你一定是昏了头了。告诉你,别忘了我提醒过你多次了,不要把情绪带到学校里,带到课堂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再来。还有,你必须找到学生的家长,向人家赔礼道歉,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安抚好他们。要是人家找来……。校长递了枝烟给他,他接过来用手指捏了捏,很柔软的感觉,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味道刚刚好,他表情松弛地点着了它。校长的样子他其实一直挺喜欢的,跟他叔叔有点像,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学,他不喜欢叔叔的胖乎乎的样子,反倒是挺喜欢校长的这张胖乎乎的温和的脸,这是他一直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叔叔是个精明的家伙,所以后来中风了。而校长呢,虽然笨了点,可是身心健康。校长批评他,他从来都不生气。这老头今年底就要退休了。他会想念他的,这是个好人,有时愚蠢了点,但心地善良,总能原谅犯错误的年轻人,比如他,原谅过不知多少回了。想到这里,他不免有点伤感。校长可能是感觉到了些什么,很官腔地提醒他,明天,我要听你的课的。什么课?就是今天上的这一课,有些老师反应你讲的有些特点,但放的录像片似乎有些问题,就是那些大象的……。他准备离开了,校长又叫住了他,“那个孩子,我让他先回家了。”
开了门,他发现只有厨房灯是亮着的。已经是晚上六点钟了。他把雨伞斜着搁在门后面的鞋架旁边。外面的雨早就停了。儿子的房间里,被子还没有叠起来,但显然人已不在家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在客厅的茶几上,看到了一个纸条,上面有儿子的字迹,铅笔的,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还是那么工整:“爸爸,我出去了,妈妈没回来,手机也关了,我想找她说说话。找不到她,我就去找你,我们说说话。”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这时候,她的手机显然已经开通了。他略微松了口气,“你在哪呢?”她迟疑了一下,声音平静地说,在外面。“儿子呢?”他尽量声音平和地问道。她愣了一下,不是在家里么?“他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我手机没电了,刚找到电源……。“他出去了,说是想找你说话。”什么时候的事?“上个世纪。”他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就不说话了,那边也不说,过了半天,他才放下了电话。他默默在看了看整个房间,想了想,然后起身把客厅里的灯打开了,灯光明显有些刺眼,同时一种奇怪的饥饿感从腹部漫延开去,一直弥漫到嗓子那里。他重新拿起电话,拨了母亲家里的号码,等了一会,没有人接听。他穿上外套,手里握着自行车的钥匙,锁门出去了。
街上湿漉漉的反映着两侧的灯光。他骑着自行车慢慢地行进,车轮跟地面接触的地方传来那种令人心烦的细碎声音。下过雨之后,天气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凉,尽管已经是十月初了,可是雨后的空气里仍旧残留着些许温暖的气息。这种温暖在他看来实在有些古怪,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感觉到某种不能适应的残忍。从街口转出来,到了比较宽阔的马路上,路灯是最近才重新换过的,看上去有点像昆虫的触角似的,高高地伸到空中,散发着晶亮的光芒。在这种好看的场景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去了哪里,还有比这更令人沮丧而又不安的事么?没错,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是轻易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他知道回家的路线,也知道亲戚们的住址,他能自己坐公共汽车,身上也会有些零用钱,他什么都知道的……可是,现在他在哪里呢?他想说些什么话呢?他的头一定是不疼了。想到这里,他停下来,伸脚踩着马路边的石头路沿,拿出手机给儿子的老师打了个电话。老师说你儿子今天不是生病在家休息么,根本没来学校啊?他只好胡乱客气了几声就挂断了。他继续骑着自行车往前走。儿子五岁的时候开始得了头疼病,非常奇怪的一种毛病,去过几家大医院检查过多次,都说没什么问题,但头疼还是会时常折腾这个孩子。能缓解这种症状的,有时候只有恐龙了。儿子是个恐龙爱好者,从四岁开始就喜欢琢磨恐龙,到如今他已经收集到国内几乎所有中文版的恐龙资料、光盘,还有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恐龙模型,他最崇敬的是霸王龙,而最喜欢的却是翼龙,在他看来,父亲生活在白垩纪晚期,而他自己呢,却是侏罗纪的。完全的时间倒错的安排,当然那是儿子小时候的想法,现在他是不会这么说了,他甚至很少会对父亲提起恐龙的问题,不过他仍旧一如继往地关注着那个早就不存在了的恐龙世界,甚至还写了几篇关于恐龙的作文,在他自己的日记里,最近一篇,是关于恐龙灭绝的,结尾写的是一个恐龙蛋掉到海水里的情景。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学校门前。快要七点钟了。教学楼三楼,初三年级的那些窗户还都亮着灯,远处看去像似一道白亮的“一”字。这道亮光投射到操场一半左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模糊的光块。一楼的值班室灯光也亮着,借着这片光,可以看到楼下的领操台,他注意到,领操台上有两个不大的身影,并排坐在那里。因为背对着光,他们的脸以及身体的正面是黑暗的。其中的一个,手里似乎拿着一根有些歪扭的木棍,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摆弄来摆弄去。他们在说着话,是两个孩子,声音不高,而且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不过他已经感觉到,其中一个声音,正是儿子的。他把自行车停在校门内侧,然后顺着墙走,走到教学楼下面,再转向领操台那边。他慢慢地走过去,脚步很轻,像夜里无家可归的野猫似的。几分钟后,他来到了他们的后面。他们显然没有感觉到有人来。听起来,他们似乎已经聊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他听清了另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就是那个刚被他打过的男孩。“你爸爸在这里教什么的?”他儿子若有所思地答道,生物学。“是哪一个?”儿子告诉了他。那孩子重新打量了他儿子一下,“哦,不像么。”嗯,他儿子说,我长得比较像我妈。“怪不得你知道那么多恐龙的事儿……你爸挺凶的。”他儿子点了点头,嗯,知道。“可他讲的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他在家里老给你讲吧?”儿子摇摇头,不讲,他事情多,没什么时间,我是自己看。“……他看起来倒是像个好爸爸。他上课时说话的样子,挺逗的。”儿子表示自己没见到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他打你么?”儿子想了想,从来没有。“不会吧?”可能是因为我有头疼的毛病吧。“头疼……是紧张的?”儿子摇摇头,想了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说说话就好了,有时候说话也不好。“你这毛病倒是挺怪的……”我从小就这样了,很小的时候。
“你怎么现在才来找你爸?他早就走了……我看见他走的。”儿子说,我是去找我妈的,没想找他,后来是路过这里,就过来看看,以为他在。“你妈下了班不就回去了么?”也没什么,儿子犹豫了一下,就是想跟她说说话吧。“哦,你倒是挺怪的,跟自己妈说话也要找出来说。”我有好几天没跟她说话了,儿子说道,跟我爸也是。“我爷爷死了。”儿子看了看他。“好多天了,老死的,就是活到顶了,也没病,就死了,就是闭上眼睛,跟睡觉似的,不醒了。反正我不能再跟他睡一个床了。我奶奶又聋又瞎的,他们要把她送到养老院里去了,这回没事儿了。也不用人管了。我这几天特自在。家里天天都是一堆人……我妈过两天就来接我。她男朋友有车。”那,你爸呢?儿子显然多少有些惊讶了。“他?谁知道,他可能是……四海为家吧。不过我妈说他早就给人埋了。他以前,在这里是很有名的。没人不怕他。可我记不住他长的什么样……”那孩子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你怎么还不回去?我告诉你,晚上坏人多,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客气跟你,他们是什么都不多说的,他们就这么……”说着他抬起左手做出要卡儿子脖子的姿势,但并没有继续这个动作,只是停在那里,儿子没有动,不声不响地看着他,他慢慢垂下手臂,“这就是一招,你会么?不会?嗯,看你也不像……要是你以后想打架了,找帮手,就找我好了,怎么样?你不想……我看你啊,还是回去得了,跟你爸说说话,跟你妈也说说话……你脑袋还疼吧?哦,不疼就没事儿了。”他这么说着,另一只手握着那根棍子用力敲打了几下领操台的水泥边缘,发出那种清脆的响声,在黑暗中的校园里回荡着。
【论坛讨论】
生铁
我是沙发么?
每次家里有点风吹草的时候,
少一“动”字
你爸呢?他儿子显然有些惊讶了。
是否多了个“他”字?
挑了两个错。
一个像夏天刚过完的某一天的深夜,清新,但是黑暗,而且到夜里还是开始感到冷了。
生长中的青年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人对人的了解,或许还没有人对象多。
孩子们的对话把握得好。
酒童
顺从的、茫然的、找不到理由的、极想抗辩的信仰问题,在开头的年轻的象群们的叙述中被提出来,又在最后两个儿子的对话里凸现后,解决了?没解决?不想解决?赵松兄说过,说作者不需要,也不可能进到小说人物的“里面”去。(胡安.鲁尔福这人就很自信,他很武断,也较为准确地‘进去’了)。不过,够了,这样写足够了。
好!整篇被压抑的调子给拿住了。“隐”在里面的两个妈妈和被埋掉的另一个爸爸,很活。感觉老师的叔叔有点多余,好像就为托起校长而存在。校长写得很成功。
看了一遍,只想到这些。对不对另说。
想起什么,以后再说。不过,第一遍读后的感觉是准的,就我而言。
赵松
每次家里有点风吹草的时候,
少一“动”字
你爸呢?他儿子显然有些惊讶了。
是否多了个“他”字?
挑了两个错。
一个像夏天刚过完的某一天的深夜,清新,但是黑暗,而且到夜里还是开始感到冷了。
生长中的青年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人对人的了解,或许还没有人对象多。
孩子们的对话把握得好。
都改过来了。两个错误。第二个其实是想把他再留一下,但并不好,反而多余了。删了是对的。
赵松
顺从的、茫然的、找不到理由的、极想抗辩的信仰问题,在开头的年轻的象群们的叙述中被提出来,又在最后两个儿子的对话里凸现后,解决了?没解决?不想解决?赵松兄说过,说作者不需要,也不可能进到小说人物的“里面”去。(胡安.鲁尔福这人就很自信,他很武断,也较为准确地‘进去’了)。不过,够了,这样写足够了。
好!整篇被压抑的调子给拿住了。“隐”在里面的两个妈妈和被埋掉的另一个爸爸,很活。感觉老师的叔叔有点多余,好像就为托起校长而存在。校长写得很成功。
看了一遍,只想到这些。对不对另说。
想起什么,以后再说。不过,第一遍读后的感觉是准的,就我而言。
可能是因为他七岁时起就由叔叔抚养成人的吧。但他并不喜欢他叔叔。所以他会有些喜欢校长。
黑天才
我和酒童意见不一样,校长那一节我倒觉得是最弱的。如讲大象,在家里的父亲和儿子。结尾三段的转折我觉得是最棒的。镜头完全由第三人称的他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上(这个他,更像是第一人称的”我“),这在前面营造的气氛和叙述角度上是难以想象的。
酒童
嗯,黑天才,那不是问题,读者有很多种理由感觉小说里面人物的好恶。
可能因为赵松后面三段的不动声色,角色的切换很自然。这是他的功力。胡安也有这手段,他的《那个人》就是这样,“他”、“那个人”,最后在读者不知不觉中,又切换成“我”了。
陈卫
研究作者的写作动机真是件好玩的事。作品背后的故事,促成作品的真正原因,真的很有意思,哪怕这谜底与作品这个谜面隔得再远,我也会觉得这层关系是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这加大猜测和想象。所以,这篇,我猜赵是为儿子写的;其实这也几乎是一目了然的,我只是想说,它已经事先排除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对儿子的情感,使心境回到零点或空白,才有了这个主题帖里的一小方块“故事”。
我倒觉得最后一小节小孩的对话不是很准。陈述的语调过于老练,尽管我知道孩子自有其老练,但还是具备着孩子自身“特殊的老练”,就像塞林格写无比天才的泰迪,也非常重视其“特殊的老练”;最后对话的节奏也很奇怪地急了,老赵你再看看。
结构、起转,还有语言,毫无疑问都很舒服,写完也肯定很舒服,因为它文眼深藏,就像把一罐上好的蜂蜜不动声色地密封,放到了阴凉处。 赵松
对话的问题确实存在。我有点代他说话了。已经重新弄过。
老残
语言真的很舒服,细节处理很到位,至少没有那种让我停下来打嗝的感觉。
不过结构上好象还可以再复杂点。这样就结尾了也有点可惜。
生铁
老赵的小说,特别是这篇的感受,很容易让我想起Chet
Baker & Paul Desmond的布鲁斯专集Together。
黑天才则一直给我种很“入世”的感觉,自弹自唱,从不搞电子音效,有点像罗大佑和盘古乐队的某种怪异混合体。
而我多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Samhain的The
Birthing一样啊。
高原
很早就看完啦,不知道怎么说。读这个小说时的感觉跟我以前读库切时的感觉特别象,暮气沉沉,阴霾不散。这个小说象五十来岁人写的,天命之年话沧桑,就给我一这么个感觉。我觉得赵老师再这么写下去,我们应该掂量掂量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写了,谁也不想当垫背的。
生铁
我前一个帖子为什么谈到音乐,就是想表达这个。都是低沉阴郁的。但老赵这个表达上更像BLUES。
郭辣辣
第一感觉就是跟大象有关的。不管接下来写的是什么。
小马甲
不错。但结尾不大好。就你而言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些,像这样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结尾是对自己不大负责任。
赵松
谢谢,这是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水平了。我当时的想法很明确,就是让这个小说在声音里结束。
腊月16
写得真好,新手学习了!
我开始是掠过第一段读的,因为第一段读的时候有点混乱,可能是没读惯类似的小说。以儿子作为代表贯穿始终,通篇气氛哀婉忧郁,很感人。儿子的头痛在象征,或者是在预示着什么。我曾听说夫妻关系失和会导致孩子发生莫名其妙的疾病,比如视力下降或一些神经或精神性的障碍,作者对此应该有体验,或者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通篇最玄奥的地方就是儿子的头痛病了,隐隐地蓄势待发却又始终没发,但已经等于发了,因为借另一个孩子的口说了出来。这篇作品好像是阐述家庭问题的?我只是觉得一多半对话不像是孩子的口吻能说出来的,因为对话太长太多了,我觉得应该没有12岁的孩子能对某个问题探讨那么久,而且语气完全是成人式的。那个能在水里呼吸的怪兽加进来也挺有意思的,很配。不过写得还是很好,我觉得够我学半年了:)
新手,发言的意见等于学习,楼主不要见怪,我刚开始学着写几个月而已。 还有,我觉得结尾相当好,有余韵,有回音。
赵松
关于孩子对话是否成人式,这个我有过充分的考虑,我儿子目前七岁,他说的话,常常是令我吃惊的,且不说他成不成人式吧,他总能很直接地说出大人们不好意思说的话,这样,我推算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说话应该比这个小说里的孩子说的话更让人意想不到。当然这里的这个孩子毕竟不是我儿子,就像那个老师不是我一样。
杨昌文
喜欢这篇小说,像前面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样,够我学半年的了,或者更长。
冯与蓝
老赵的细节描写是一大亮点,浓郁繁复,又冷静坚实。一些日常随处可见的意象,像翻花绳似的,被重新发现了。
“教学楼三楼,初三年级的那些窗户还都亮着灯,远处看去像似一道白亮的“一”字。这道亮光投射到操场一半左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模糊的光块。”
对的,就是这个样子。并且,这样纯粹的环境描摹非常自然地带出了感情,对孩子的爱。悄无声息。夜晚的寂静衍生出的孤独感,潜藏着的,是言外之意。同时故事又在对话里隐约地铺展开来,非常有耐心地一点点抽丝剥茧。一个圆致的句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诸如此类俗套的评价就不赘言拉。
亢蒙
这篇感觉好像是黑白电影,语言在强度上变化成了柔软的可触摸物。在阅读的过程中,作者老练的叙述水平让小说整体出现了很好看的纹理,读起来口感更加偏向奶油,松软但是又不垮。小说中的一些意象映射很有交叉的复杂性,多少对理解造成了混淆。个人还是觉得小说的结尾有一点点的紧。
赵松
谢谢亢蒙……其实从整体结构上讲,这个小说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不充分的地方,虽然并不是很明显,但事实上有些因素还可以再拓展出一些空间,那样的话会更饱满而有纵深感,有时候留白过多也会减弱结构的力量。
陶北
一直喜欢赵松从容细致精确的文字营造出的那种气氛和味道。你如果出一本散文集也许会很受欢迎。
我的儿子马上12岁了,我们关系不错,但我不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