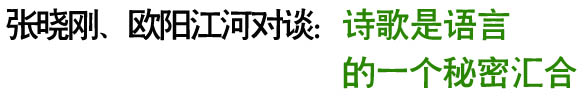欧阳江河:著名诗人。原名江河。1956年生于四川泸州。现居北京。出版有《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站在虚构这边》。欧阳江河的存在,使四分五裂的诗坛形成了某种秩序。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并非一脉相承,而是时有变化,多采多姿。《汉英之间》的预言,《玻璃工厂》的寓言,《最后的幻象》的茫然,《傍晚穿过广场》的反省,《谁去谁留》的日常以及献给庞德的《公开的独白》等,均为当代诗坛的优秀之作。
张晓刚:著名画家。1958年生于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现生活、工作在北京。1997年荣获英国COUTTS国际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亚洲当代艺术家奖。中国后89’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代表作品有《全家福》、《大家庭》、《血缘系列》等。参加的重要海内外展览包括有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等。
张晓刚: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制的年代。
实际上,复制是今天普遍遇到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种现实。
人和人在复制,想法也在复制,
从想法、行为、物品到很多习惯都在复制。
复制绘画也就变成了一种人存在的方式。
欧阳江河:诗歌是语言的一个秘密的汇合。
但哪有这么多秘密啊?
诗歌是反语言的产物,不是语言本身正常的交流、沟通。
它是交流和沟通的剩余物。
我们用语言交流、沟通,表达完我们自己之后,还剩下一点东西,
这个东西旁人视作垃圾,但诗人把它当成宝贝一样,
保存起来,形成能量、秘密,然后把它汇集起来。
路的尽头,铅灰色的铁门上写着绛红色的C2009。这里是靠近五环京城高速一个僻静的酒厂艺术社区。空气中偶尔飘过松节油味。四下找了找,并未发现门铃。我再次打电话给屋子的主人张晓刚。开门的是摄影师李广锌。穿过一个面积不大,但类似于天井或者庭院的地方,正屋门口还有一棵小树。按照欧阳江河对老友的谙熟程度,“现在是世界杯期间,张晓刚晚上都是要看球的。他上午睡觉,下午才到画室工作。”对谈时间往后顺延。直到有了一个空档,世界杯决战前一天。下午3时。我们都到张晓刚的画室。
室外已经是闷热异常,但室内却显得相当凉爽。张晓刚正在接听电话,我们点头示意微笑。长方形画室内,三面墙角置放着尺幅较大的作品,画架上的作品还在起稿阶段,画面上勾勒的是像学校每周一都会升国旗的地方。地上几个纸箱,装满了油画颜料、松节油、画笔和笔刷之类的东西。张晓刚告诉我,这是他正在进行的新作系列:《风景》。场景来自他父母家里的一张沙发、电视或者是餐桌上的器皿等等,画面上当然还有他独一无二的标记:带着电线的灯泡。无论它是垂直还是横躺。墙上挂着他的新作系列,用数码相机从电视上截取下一些晃动而模糊的画面,把照片喷绘之后,用银白色的荧光笔,抄写一段中文或英文的文字,譬如但丁的《神曲》。张晓刚带着一种神秘又有些诡异的微笑说:“这是去年回昆明时的灵光一闪。开始画《大家庭》,也是因为回了趟昆明,昆明是给我绘画灵感的地方。”
张晓刚又在接电话了,说着四川话。
欧阳江河戴着墨镜,中国红的T恤衫扎进乳白色的裤子,腰上系着黑色皮带。欧阳江河显得精神而有生气,用张晓刚的话来说,就是“很阳光”。从他嘴里总是蹦出一连串滔滔不绝的措辞,只要开口,音量就会迅速提高,速度节奏不断加快,与此同时配合各种表情与手势。
张晓刚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淡定与冷静。交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说话不多但非常清晰。兴奋起来至多笑几声,香烟总是一根接着一根。他经常使用“感觉”来描述他的情感,用“虚幻感”描述他的成功以及令他倾心不已的绘画大师。“暧昧”、“阴郁”、“恐惧”或者“学画时像着了魔”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
一切因为《同志120号》
欧阳江河:我和画家、音乐家的交往很多,他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张晓刚的作品在纽约苏富比拍卖的时候,我与诗人翟永明、现在画廊的黄燎原都在现场,大家非常兴奋。我对当时拍卖的场景可谓是记忆犹新。《同志120号》从20万美元开始报价,底价是35万美元。等20万美元一报之后,拍子都纷纷举起来,30万、40万……一直涨到9792万美元……
张晓刚:我的第一反应是:啊,疯掉了。对我来讲,拍卖是件别人的事。进入市场以后,一个新的体系出现了。这个新的系统完全是我们过去没有任何经验的拍卖系统,或者说是市场系统。拍卖是一个二级市场,只是说这两年的市场更多体现在拍卖上,而不是一个正常的画廊市场。这个系统对我来说很陌生,是收藏家和收藏家之间运作的一个结果。这与我的艺术怎么做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它可能从利益上给我带来好处。
欧阳江河:除了拍卖系统,有藏家、卖家、炒家、画廊,包括一些经纪人以外,还有一股力量的介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的介入。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的绘画已经很好了,但媒体没怎么关注。由于没有进入拍卖市场,它更多是艺术家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社会公众关心的事情。消费行为对公众的心理、舆论的导向和社会时尚,都会有很大影响。媒体会把自己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加进来,这个角色曾被策展人和批评家占据。媒体的作用,实际不是对画家本人怎么画画产生影响,而是对观众怎么看待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价值,怎么去给他们作历史定位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和市场拍卖价形成了一个“同构”关系。这非常有意思。只有在消费时代到来的时候,才可能产生非常有力量的影响。
成功,是一种个人虚幻感还是集体困境?
张晓刚: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变成了另外一种符号。别人选中了我,我就成为一个游戏格局里的另外一个人。
欧阳江河:别人对张晓刚绘画的成功,在于他的画卖了多少价钱。但对我来讲,可能张晓刚的画一分钱不卖,他也是成功的画家,这是我从他绘画的气场来看。你刚才谈到你的画卖这么高的价钱,但感觉与你没有什么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困惑。如果你的画要是卖不起价钱,你觉得也是一个困惑。但是社会上不会这么看,这个是对张晓刚的一个歪曲。他的成功可能是由于社会的误解带来的,所谓社会意义上的成功。收藏家要炒他,因为他的画太值钱,媒体要炒作。我指的是社会意义、媒体意义上带来的粗俗化的成功。所以成功和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成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成功”的概念造就中国整体素质往下跌,就在于它的粗俗化、非文化、消费化,这些不是贫穷带来的,不是失败带来的,也不是封闭带来的,而是成功带来的。现在大家都在谈成功,把成功定义成一种非常偏执的,简单化的、量化的,而且是庸俗的概念。
张晓刚:从社会的角度讲,我是成功了。但我觉得很虚幻。可能我会越来越有名,以后我画什么都不重要了,主要是签名(笑)
欧阳江河:成功,已经变成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集体困境。成功带来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有失败者才能感觉到。一个没有成功的人肯定被成功的人压迫,一个画卖不起价钱的人一定会被画价卖得高的人压迫。我指的是市场经济上的压迫,或者失落感、挫败感、虚无感。一个成功者能够感受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快乐、创造感以及创造历史那种主宰的感觉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人的成功带来新的失落感、新的困境、新的无力感和失败感。也就是应了萨特那句话,“胜者为败”。现在整个中国文化,从媒体、时尚的意义上讲,宣扬一种成功者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困惑最后有可能是来自于成功。
不断复制的年代
张晓刚: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制的年代。实际上,复制是今天普遍遇到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种现实。人和人在复制,想法也在复制,从想法、行为、物品到很多习惯都在复制。复制绘画也就变成了一种人存在的方式。我也不可能只画一张画。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画了两个系列。从1994年开始画《大家庭》,一直画到2000年,差不多有6年时间。2000年的时候,不太想画画。从2001年更多的精力是开始画另一个系列《失忆与记忆》。一个艺术家是有局限性的。别人对你的要求这么多。但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方向,不断往前走,我不用“变”这个字,但要往深处走、宽处走,总之是往前走。所以从《大家庭》到现在,我尽量把自己的路走宽一点。这个画不动,我就再画另外一个。而且复制本身也是当代的一种特征。画《大家庭》时,我可以画一百个大家庭,但不是简单地拷贝,而需要先确定一个观念,在这个观念里面慢慢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或者叫做风格。当代艺术需要一定的量,这和古典艺术不一样。比如《蒙娜丽莎》就一张画,可以画4年。而且原来全国美展的习惯,就是每人展出一张画,一整年都得对付这张画,然后可能得奖,接下来又会画另一张画。这种创作模式,把其它的画变成了习作。创作和习作分开了。而当代艺术就不能这样做,每一张画都是一张画,而且要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地去做。要有一定的量,才能完整表达艺术形象和观念。
欧阳江河:怎么来定义创造?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是不是画一个谁也没有画过的东西,才叫创造。现在人们把“创造”和“创新”等同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有人说过,“我们已经被创新这条狗撵得没有地方去了。”创造力实际上是在不停地重复,在旧有、已有的过程中,达到完美。也就是画别人画过的、说别人说过的话、爱别人已经爱过的人,这个可能是真正的创造,因为我比别人做得更好。比如写诗,今天写口语诗,明天又改成写另一种,难道这才叫做创造吗?庞德一辈子就写一首诗,叫《诗章》。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章,充满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力,而他用一生来写。
张晓刚:我同意你的说法。创新可能是一种形式上的翻新。但我更看重的是能否创造一种文化。包括创造一种符号,一种精神指向。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量来积累,才能接近主题,达到一定高度。这其中肯定包括复制、重复。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复制,但好像忽略了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要把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准,必须先有一个量。在西方这些不会受到质疑。如果进入一间画室,发现艺术家的作品有很多风格,你可能觉得这个艺术家太有活力了,但我认为这个艺术家很没出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他可能有很多种风格,但不是一个有创意的艺术家。
诗歌,它是语言秘密的汇合,是一种剩余物
欧阳江河:从整个艺术史和诗歌史来看,主要的艺术家和诗人都有自己的标记。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是,不处理词与物的关系。我想把物质性在诗歌里面复活起来,处理词与物的关系是我的一个诗学抱负。比如我写《玻璃工厂》。它的透明感,也就是这种物质的特点,在我写的过程中反过来影响我的语言风格。就像我不能用写手枪的语言去写玻璃,用写水的语言去写一座山或者石头。像很多诗人偷懒,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语言、同一种速度、同一种修辞方法。我写玻璃工厂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透明的语言。比如:
“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隔开就是一种观念,把我们的声音隔开,但中间如果是书就不行了,不能阻挡我们的视野。然后: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
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
这个透明的特点语言从哪里来?就需要回到玻璃本身。存在和不存在、看见和看不见,我把这种东西写成原诗。这个在当代诗歌里面是独一无二的。诗歌是语言的一个秘密的汇合。但哪有这么多秘密啊?诗歌是反语言的产物,不是语言本身正常的交流、沟通。它是交流和沟通的剩余物。我们用语言交流、沟通,表达完我们自己之后,还剩下一点东西,这个东西旁人视作垃圾,但诗人把它当成宝贝一样,保存起来,形成能量、秘密,然后把它汇集起来。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而是非常恐怖的一件工作。这个工作不像绘画,到一定时候可以变成商品、消费品。诗歌不是一个东西。它是“虚无”、是“没有”、是“漏”。比如张晓刚绘画中关于“电”的东西。讲到个人记忆或者公共记忆的时候,“电”就特别让我敏感。它带来的联想就是“漏”,就是不够、不足、欠缺,它引起的是一连串词根的联想,“漏电”、“漏水”、“漏雨”、“偷税漏税”。“漏”是社会的一个现实,因为那时质量不够、物质匮乏、需要修补。就像那时有人偷电,本来100瓦的灯泡,就只剩下50瓦的亮度。所以这个联想指向我们的文化记忆,定义我们当时的现实。
张晓刚: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剩余物,完全颠覆了以前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原先我们肤浅地以为诗歌就是玩语言、玩词。诗歌是一种纯精神性的东西,是很神秘的。它可能要借助语言,但不是在语言本身里,要超越语言本身。“剩余”感觉特别准确。在我们这个实用的时代,已经没有给诗歌留下多少空间了。按照这个理解,诗歌就是垃圾。这个时代的人会觉得它对生活没有什么用处,不像以前那个时代,说起某人是诗人,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觉得他的大脑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情感也和别人不一样。
欧阳江河:现在有的诗歌是拿来作表演的,我特别讨厌这样。
张晓刚:曾经有人说我的画很恐怖。好听一点是“恐怖美学”。我承认我的画里有恐怖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有这种恐怖感。别人看我的画,有人会惧怕这种恐怖感,有人就会觉得有神秘性。但如果看习惯了,就像看恐怖片,一开始看,吓得不得了,但慢慢看,大家好像还离不开恐怖片,还觉得拍得还不够过瘾。单纯从恐怖的角度讲,我觉得是习惯问题。习惯以后会发现其它东西。我觉得一个艺术品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或者叫它的暧昧性。如果只是简单地告诉别人一个快乐的故事,就会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只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认为好的艺术,就是在于它的暧昧、多重性和多面性。诗歌里面有没有多义性?
欧阳江河:当然有,就是诗歌的歧义性。
张晓刚:你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进入、去体验,这才是艺术。不然就像一个口号,什么都说清楚了,不用自己去体验了。
欧阳江河:你比较酷。
张晓刚:这是我的性格。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气质画出来。就像我和欧阳江河在一起,一对照,我就不可能画很强有力的、很阳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体会不到阳刚的美。我可能更多体会到一些比较阴郁的东西,这个应该与我的气质有关。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从小就有恐怖感。
欧阳江河:我跟张晓刚在气质上有很大差异。比如他说的恐惧感,或者是阴郁性,那是没有具体指向性的。不是由哪一个具体原因造成的,而是体现他一种内在气质、精神气质。人不可能没有恐惧感。我也经常有恐惧感,但是是有具体指向性的。我估计张晓刚说的怕,如果他面临具体的东西,他可能不怕,但如果没有具体指向,他反而会怕,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可能是一种精神性的、气质性的。人类的恐惧感就在于他不知道他恐惧什么。恐惧是没有对象的。
张晓刚:我要知道的话就不恐惧了。
欧阳江河:你看的家庭照,都有幽灵气息,有隔世、来世的东西都是已经死掉的和活着的人。
张晓刚:哎呀!(笑)幽灵……
从误读开始
张晓刚: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通过对西方艺术的误读,然后慢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在写关于马格利特那篇文章,最早认识他,完全对他的情况不了解,完全不懂为什么这个烟斗也是艺术。到后来,通过学习,眼界的开阔,走到今天,马格利特就像变成了我的朋友。很多大师在我心里,从很神圣的地位,慢慢变成一种很亲切的地位。现在我重新读他的画,我会用一种艺术家的心态。我喜欢马格利特和籍里柯那种虚幻的感觉。我从马格利特那里学到最好的东西:把一个熟悉的环境、物品或者人物,进行虚幻处理。这是一种艺术的语言,也是我所理解的艺术的一种魅力。也就是通过使用“内心化”的语言方式去描述我们的生活,去关注那些常常被忽略的心灵。虽然我画人物,但我不是肖像画家,我不画某一个具体的人,我画我理解的某一类人,也不是所有的人。
欧阳江河:从《大家庭》系列开始,你的绘画有一个重要主线:处理一种历史记忆。这段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个人和群体记忆的综合。你用1950年代的记忆照片,把它作为一种绘画对象、绘画材料、文化材料,同时也是一种视觉符号化的材料。我觉得这是真正在处理文化时期的记忆。在这方面,张晓刚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画家。也就是说,有一种具体性在里面。有时候,如果作品脱离具体性,放到一个更抽象或者更超脱的语境里去看,它会更好。这也和诗歌一样。有这种情况,有的诗当时写出来不得了,造成很大轰动,10年之后,时过境迁,再看就会发现漏洞百出;还有一种诗,当时不错,但过了10年或者15年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因为它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任何绘画、诗歌的创作都和当时的语境、社会风气、个人的遭遇、处境,包括经济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因素相关。比如杜甫的诗。有人认为他中期的诗写得好,因为身临其境,写了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当时的现实、他的家庭以及个人的艰难,当然写作上也很不错。这更多是一种知识考古学和社会考古学的东西。杜甫到了晚年的诗歌,他写《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的时候,个人的具体处境已经不在了。他更多是考虑诗歌本身,也就是作为诗最核心的是什么?尽管已经隔了几千年,我们再读他的诗,就会感觉到这是永垂不朽的诗。这是关于诗歌的诗歌。他的贡献就在于给诗歌本身作定义。这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1980年代我们开始写诗,也是受到非常复杂的影响。我们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和张晓刚他们受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还有所不同。比如,你们通过印刷品来受到影响。虽然不是原作,但精神氛围还在,可能没有了一些绘画表面性的东西,但它还是一个拷贝,还不会是一种弯曲、误读。翻译是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中间就会损失很多东西。翻译也是误解、误读、错误的产物,尤其诗歌是不可能被翻译的。但没办法,因为我们当时又不可能去读原文,直接面对的只能是翻译。当时对我很震撼的一件事,就是我读到荷尔德林的诗。他是德国一个非常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到现在为止,他的德文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是太困难了,像是密码一样的语言。但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用的是文革语言,诸如“东风浩荡”、“沿着山路群山起伏”、“沿着小路归回到家乡”这一类语言。太恐怖了。意思可能是没错,但由于选用表达的词汇,词与词之间声音的、暗示性的、意象的、递进、聚焦的关系全没了,只剩下意思。但是对于诗歌来说,意思是它最不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