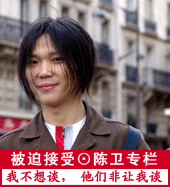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在福楼拜的作品中并不鹤立鸡群,可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它是作家流传最广的代表作;绝大部分读者,言福楼拜首先乃至唯一谈论的必定就是《包法利夫人》,似乎《包法利夫人》成了理解福楼拜的通行证。一方面,这证明着作品离开作者之后不可控制的命运,另一方面作品引发的官司或道德争议也助其一臂之力——《洛丽塔》的幸运与此异曲同工。
“客观、真实、科学”,是与福楼拜紧密相连的几个关键词;然而只要我们不想欺骗自己,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现实与这些理论归纳并不完全相符:被“新小说派”追认为“客观、真实”理念肇始的《包法利夫人》,其中对“典型”的执拗,及其所致的一些与“客观、真实”背离的现象,常常让我思考他在本质上有多大的“现代性”——尽管“现代”与“古典”的区分并不那么重要。以更大的“客观、真实”为名流传的《萨朗波》,我又常常疑惑在最大的态度和视角上,即在对萨朗波这个人物的态度上,它如何称得上做到了“客观、真实”;至于《情感教育》,我甚至觉得它重又回到了浪漫主义的老路上;而《圣?安东的诱惑》,其体裁其实已不是小说,它似乎更想成为诗剧或史诗《浮士德》的法国版,其文学野心更是与“客观、真实”距离遥远。
是福楼拜的作品确实不够,还是理论归纳的粗疏?其实,这两个疑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发现,这些理论归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文学言论,较少地来自他的作品。这不是一句平淡的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因为福楼拜一系列陈述其文学观念的言论,越来越比他的作品还要重要,其重要性首先因为它们出现得非常及时,对时代(当时以及至今)极具意义,“科学、客观、真实”、“小说家不应该在作品中对这世界上的事物发表议论”、“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凡是真的都美”、“形式和思想是同一件东西……思想越美,句子越铿锵……思想准确,语言就准确。”、“像诗一般有节律,像科学语言一样精确”等等,这些所有指针都指向“客观、准确、真实”的言论,使当时浪漫主义泛滥、情绪夸张宣泄的状况在文学上得到冷静的约束。这种“应运而生”对观念的影响力的推动非常重要,所谓“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当然,这不是暗示福楼拜的“投机性”,相反,自然是他的一切禀赋、刻苦努力以及广泛深刻的阅读和思考才获得貌似巧合实质犀利的眼光。与“及时”相连,他的严谨作风巩固了他的观念。众多读者深知他对艺术对创作的严谨态度并为之所震动。这种严谨为他的言论提供了“这种态度系统之下的产物不可能草率”的规则保证,并信任其作品与其观念必定统一。
强调他言论的重要性,并不是为了来评价他的作品本身,无疑地,福楼拜的作品都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他的文学观念,只是与他坚实强硬的观念相比,一些作品的局部显得涣散、乃至恍惚。追究起来,这委实情有可原:在浪漫主义尾声的风口浪尖,福楼拜通过阅读思考,在理性上清晰预知了未来的方向,但是,“明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做到”,少年时期浪漫主义对他的深重影响,不是那么容易摆脱,他往往不能自拔地染着浪漫主义的色泽。情感上的悖论也在作祟:越想摆脱的,正是越难摆脱的;这一点在事实上也有迹可循:他曾把雨果追为偶像;这些上一代风格的集大成者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同时必然携带出一些铺张渲染的气息,但是他们强大的精神旋涡往往覆盖着反对者的思维,使掣肘者不能不时时回到他们的光环之中。巨人的反对者必然是艰难的,即便他具备与巨人同样的气力,也往往会在过程中重新成为对象本身。
后来者则更可能择取前人对自己有利的观念加以夸大以便利用;这充分解释如今理论界对福楼拜的归纳所得与福楼拜作品现实的差别。其实无论何时,观念都比作品本身更直白地展现艺术家本人。观念的传播也要远远大于作品的传播。这对艺术而言,并非不是悲哀。但这同样昭示:艺术家永远大于作品。高度为八的作品,往往需要高度为十八的艺术家。就这一点而言,作品也永远是艺术家的冰山一角。
2007年2月4日—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