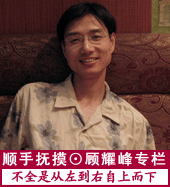虚假生活、真实表达……还是真实生活、虚假表达,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更好。但无论哪种,都表示着生活和表达存在着距离。不存在真实生活真实表达的可能吗?不可能。
我不知道别的作者怎样面对“生活的真实”和“表达的真实”。我怀疑着一个事:我们所写的那个(生活里的)事,真是生活里的吗?我们自然而然地把那些跟自己所要表达的主旨无关的、甚而伤害主旨的细枝蔓节给删减掉了,而事件往往由细枝蔓节构成,那些被删减掉的东西,它存在过。假如说这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或许只有“过去”才是真实的。我们的裁切,反而是在伤害“真实”。生活,在作品里被裁切过,对于生活本身来说,作品就是假的。
但事情往往与此相反,很多作品,会给人“真实”的感觉。人们不会去参照生活本身来考证那些“真实”是不是真的“真实”。多么虚幻啊,我们所感觉到的“作品的真实”,或者“表达的真实”,它们并不都在时间空间里的生活中存在过。作为读者,我们相信的“真实”,其实只是“感受的真实”。我们所相信的,往往是一个幻想、或者幻象。
《黑客帝国》里有一个慢镜头:两辆拖长集装箱车对撞,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把集装箱如手风琴收缩一样慢慢折叠起来。这个镜头很好看。事实上在生活里它并不成立,集装箱的耐压力要远远高于对撞产生的冲击力,两车对撞绝不会把它变成手风琴。可很少有人对它的“真实感”产生怀疑。在那种电影的那种语境下,它的表达是“真实”的。它的真实,很可能就因为吻合了人们想像中的场景。或者不提“人们”,就谈我吧,在凭空想像中,对撞后出现手风琴一样的情景会觉得挺好看的,在感受上也觉得挺真实的。
表达的真实,必然有着“投其所好”的成分存在。投谁的所好?投人们的感觉人们的感受、人们的经验。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并不要紧,文学本来就是虚构的。问题是,小说对生活来说永远是封闭的,是线段性的,是截取性的。小说的表达对真实越讲究,就越是戕害生活本身。
对不起我又要庸俗地拿女人举例子了(当然这换成男人也可以)。前一分钟女人说:我爱你。后一分钟女人说:我不爱你了。再后一分钟说:前面我爱你是真的,后来我不爱你也是真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爱不爱你。人、环境、事情、心境都在变,所以我爱你和我不爱你,都无可辩驳都很真实。包括现在我不知道爱不爱你,也是真实的。嗯,女人说的这些都可以成立。如果折射到小说里,如果我们写一段甜蜜的爱情,注意,是甜蜜的,那后面两分钟必然被删减;如果我们是写一段爱情别离,那前一分钟会变成背景而后一分钟会成为重点;如果我们是要写一段无可名状的爱情,那显然最后一分钟成了核心而前面两分钟就是铺垫。同样的一段故事,在不同的条件下,呈现出了三个“真实”。哪个真实是真的“真实”呢?在小说里,它们都是真实的。可生活只有一个。
当然还有一些悖论存在:即使对文学作品我们更看重它“表达的真实”,那又是依据什么来判定表达的东西是不是真实?我们的“感受”为什么会觉得它真实?难道不是因为有过一些生活体验有过一些生活常识所以才知道真实与否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依据什么,更重要地相信了“感受”而不是生活本身?
写下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答案:因为我们的表达,在本质上都是虚假的。它的虚假,是因为它的多样性,前后矛盾、多义反复,在宏观上构成了五光十色的混乱的“表达网络”。我们的表达,无论出于怎样的要求,它都只是阶段性目标的工具。我们表达爱情,是因为我们预设了有“爱情”这个东西。我们表达故事,是因为我们预设了有“故事”这个东西。我们的表达都为我们的“预设”在服务。而“预设”是什么?是我们一厢情愿认为的、存在于我们心里当然也有可能事实上存在的真实。而“真实”本身,也只能放在阶段性、局部的层面看待。“生活”本身,也只能注视它的局部、注视它的片断。否则,生活也是虚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即使是最可能成为真实的“过去”,也会因为“过去”所呈现的各种前后矛盾、互相冲突而显示了某种迷幻性。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在这个短文里阐明某些问题,我只想呈现一些个思考。或许这思考也是混乱的。不过我可以表明一下观点:我相信“表达的真实”甚于相信“生活的真实”,因为在“表达的真实”里,我们可以判断出“生活的真实”在哪里,而反之却不行。——这个观点也许与本文无关,但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小说里“真实表达”、“准确表达”是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