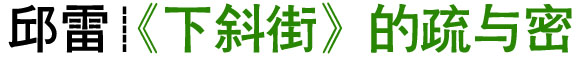《下斜街》主要是依靠情绪推动的,尽管这种情绪在叙述者和主角身上都既不十分明确、也不特别充分。它通过叙述展开的全部空间,都带有这种偏向于沉郁、含混的情绪的色彩。“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这种表面上含糊的说法,本质上却是对一种日常感觉的准确的表达:人们不管有意无意,还是被迫地模糊了时间,模糊了明确的时间分区所隐含的对生活秩序的从属意义,都更其是对当下感受的重视。只不过这一重视像摄影的聚焦一样,在突出了焦点的同时必然地舍弃焦点之后深广的背景。重视的部分明确而细密,虚化的部分则模糊和疏松,这两者的鲜明的差别和相互间的配合,对情感表达和逐步推进很有效。
不有对景物,对颜色、声音和形状的描述,尤其是对光的描写,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甚而有时会表现出过多的对物理性和几何性的形态、结构的“精确”追求,似乎超出了它理应关照的人与事的现实处境。但是必须首先承认:在这些描写中他很可能并无意于表现某种抽象的情趣或偏好,而恰恰是出于找到最符合他的内心情感的表现形式的需要;唯有如此,他才能专注于他的情感和情绪,并对其所投射的外部现实进行恰到好处的回放。在开头,回放因为密致显得滞涩和迟缓,并可能因此拖累了惯于寻求顺畅阅读的目光,使一时难以适应的读者感到疲乏和茫然。但我们只有通读之后,才有机会从整体上重新感受此时此地的速度与重量,发现它的密实并不是偏执的策略,并且乐于从情感和技巧上对其作出双重的肯定。
因为几何、抽象,反而更易达到描述和情绪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小说开头篇幅相对很长的那几段描写,就不再仅仅是故事开始之前对环境进行交代的惯例,而在结构上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它的“密”不再受到艰涩、繁复的苛责,它从一般环境描写的角色撤出,回到自身,从而重建它的意义。在这之后,以相近的手法布置在不全是连贯的叙事中的描写,也因此显得更为自信。因为有了“密”的肯定与呼应,此时相对的“疏”给了语言选择以更大的自由,使它从集中、凝练的精雕细刻之中腾出一只略显随意、松散的手,以渲染和补充叙事的其余部分,并藉以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结尾处再做任何加重的动作来避免作品整体“头重脚轻”的担忧,反而显得无甚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