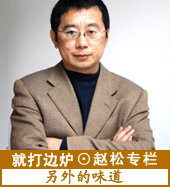——关于鲁迅的小说《伤逝》
不谙世事艰难的子君,初出茅庐的涓生,两位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年轻人,不顾阻挠一起去找他们理想中的幸福生活。然后他们失败了。首先是经济上的,都无力养家糊口,其次是感情上的,都绝望于爱,最后女主角子君还搭上了性命。这就是鲁迅笔下的爱情故事。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谈及离家出走的女人时提到三种可能,回来,堕落,还有饿死。子君的结局,基本上也在这个范畴里,只是多出了一个终极结果——死。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还指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所以子君这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对那最苦痛的状态的一种了断,也是一个彻底的解脱。只不过她的梦不是醒了,而是碎了,碎于对爱情的绝望。她没有想到的是,在现实生活压力面前,爱情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她要是的纯粹的爱,为了维护这种爱,她可以做一切能做的事,甚至可以做一个家庭主妇。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无论是她,还是她爱的涓生,面对现实生活都显得太弱不禁风了,而且都没有那种很管用的“无赖式的韧性”。
过多地强调社会的黑暗与压抑是没什么意义的。生活的艰难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是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的。老天不会因为你弱小而多给你几分怜悯和宽容,进而放你一条生路,生活的洪流每天都在近乎随意地淹没很多不能自救的落水者。这就是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哲学都不能提供什么确切的答案,更不用说小说了,所以小说不是为了某种道理而成立的,它倒是可以为了体现某种特殊的情境而存在。它可以写其伤,亦可以述其逝,归根到底,不管美好还是不美好,一切都在逝去。天真地要求完美,所以到头来必为这要求所伤。追求完美的念头只是个幻象,是个泡沫,它注定要碎裂,在这碎裂发生之后,之前那对完美的追求,以及相关的一切念想与想象,才会进入到完美的状态里。与现实的虚无相对,它无比的真实。说到底,爱的逝去,是生命逝去之前的最后一场完美的仪式。哪怕只是发生在两个平凡的小人物的生命里,也足够动人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有这么一段话:“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从这个意义看,鲁迅写《伤逝》,也无异于在做诗。也唯有这关涉爱情与生命的伤与逝,才使得这样的叙事可近于诗。涓生并不是诗人,但在伤逝之中,他的自述却可以近乎诗境。他自责也好,忏悔也罢,怀念也好,绝望也罢,徘徊也好,虚无也罢,总归都无差别了,漫无边际的苦痛时刻,就像茫茫荒野,固然有无可消解的伤痛在其中,但只要其中还隐约着一点小花朵的影子,哪怕是浮泛在无限的伤感之中,就会酝酿着无尽的能够触动人心的美,它就仿佛那蚌中之珠一样,可以在脱离生命的身体之后,忽然地闪烁出别样的更为长久的光芒来。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对于已逝者,伤痛中人无论如何言说都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就像是音乐,或者也可以说是失偶的鸟鸣,闻者足可以通过它的声音意识到哀思的无限。但与那逝者的回归完美相比,这种哀思也终归是无力的,甚至是有些多余的,以至于显得伤逝者整个生命的继续都是多余的,所谓的新生其实并不存在,如果“遗忘和说谎”具有某种引导力的话,那也不过是引导着未逝者将死亡的气息弥漫整个的世界,由这伤逝而未逝者长久地沉浸。
2008年3月2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