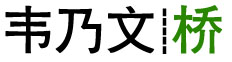他好象漂浮在空中,身体甜蜜地被什么东西压着,恰到好处地往下沉。他们的轻言细语,低低地在房子四壁内滚动。他的心一半被睡意拽向深渊,另一般挣扎着跑回他们的谈话。他转过来,发现身体不像预料的那么沉,翻开手机,还有十分钟。他几乎不想再看
一眼,啪一声合上。睡眠的姿势深深地锁住他的躯体。
他走出洗漱室,看到客厅里的所有物件一动不动。单件桌椅,冷水,自由地挤牙膏。
他变得很轻。
7点10分。
生活在改变,她仿佛已与此无关。世界在后退,树模糊地从眼前飞过,把目光远一点,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形状,越来越近,迎面扑来,直到从身边飞过去变成无法认知的物质。可怜的她突然出现在环形茶廊上,只比茶树高出一点点。阳光投在斗笠发黄卷起的大片竹叶上。洋紫荆开了一个晚上的花。它们蹲成一排,或者是这一排中的某一棵。它趴在陌生人黑色西装背部、高肩膀、楼房中空出的那一间。它在实体的穿梭中无形地流动,像你在站牌边遥望马路尽头,突然一个盲人摸倒你。
7点06分。零星几个人等在站牌小树边。手里提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跺着步子,低头看扬起来的皮鞋尖,吐痰。7点08分有一个小女孩正等在前面一站,背着书包,和她的同伴说笑。双手大拇指伸进肩膀上勒紧的书包带里,虎口挂着,手在摇晃。她像在抱怨哪一个老师,无奈地把头昂得很高,表示自己快疯了。她蓝白相间的校服里,有一件淡淡地印着向日葵的白色T恤,贴着她小小温柔的胸部。每次她走向车尾,左手握住座位上的扶手,右手抹一下水母头耳边的一竖头发,然后叠在左手上,一起抓住扶手,正式准备好坐这趟公交车。深蓝色压褶牛仔裤像一层植物的皮,抱住细长的大腿和还未成熟的臀部。四站路过后,她就下车了。回头能够看到她对同伴的笑,朴素如她洁白的牙齿,她小小的下巴,刀削一样平整的脸庞,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些浮肿的双眼皮。她在车后窗上越来越小,直到被广告牌挡住。
早晨已经很明亮了。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城市的早晨都这样。要等傍晚的时候才能知道结果。天空是腌蛋壳的颜色。和H去万邦买书,尘埃低低地压着,车辆穿梭其间,有人在卖报纸。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从办公楼逃出来,在东东包喝粥,端午节吃上半斤饺子。大半个下午躲在万邦书店闲逛,惊奇地在慢音乐的书架间碰到对方。不知道会不会下雨。河流的肠会排出城市的所有秘密。
短信:“我在桥这边,明天来把我运回去。”
存入草稿箱。
妈妈。
拐过前面的弯就会到桥。
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识路的,东南西北搞得很清楚。身体在座位摇摆、扶手在摇晃,路边的某些奇怪的树,比如它开满花,形成一个圆球,但却如脑袋一样被劈去一大半,或者某个店铺前有昨天小孩玩耍过得痕迹,树叶撒了一圈,一个破乒乓球盖在地上。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片街区。车从这里经过,经过它得内部气息,混杂着车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力学因素所带来的身体感知、长久频繁地从一个固定点到另一个的过程中,时间所起的微妙提示作用。长久沉默的H突然冒出一句:哪里下?不知道,就这里下吧。然后感观领着他们穿过街区的建筑,在一条梧桐浓密的大街尾部找到了书店。它古朴、厚重,同时又像一顶印第安帽子那样华丽,给人轻盈的感觉。有时候会迷路,像被一道数学题缠绕住。
7点12分。拐过这个弯就会看到桥。它像一只怪物匍匐贴前方马路上,随时可能爬起来。过了桥就会到市区。那边人很多。这边人很少。河水的波浪如黑色的舌头,添着这边的岸。车饶道躲过红灯,司机像蜈蚣一样多的手在方向盘上挥舞。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几乎能够闻到昏暗的车里,所有人急切赶回家的味道,混杂着座位灰尘久积的霉味、机械味。上了一天班,拉下领带,心里想着从这辆车走下去之后的家庭生活,从下车后的第一步,到餐桌上最后一次放下筷子,每一个不可忍受的细节。
在夜色降临时,路灯洒亮人群的肩膀,所有人都被原谅。早晨他是魔鬼,傍晚他带我们回家。他今天是回不去了。腌蛋壳的天空露出一块,那里是空的,城市的这一角被四处觅食的家禽啄碎,蛋黄撒在楼盘间的空气里,像谁用牙刷沾满黄色颜料,均匀地甩在粗糙平面上,凌乱的建筑群里闪动着许多废弃的亮片,车子从某些不为人知的反射光里经过,转了一个弯,人们的身体倾向同一边。饶过这个弯,车又缓缓前行。蛋黄搅入不详的沥青。这是早晨的节奏,车停住,伴随着气门放下,过道里响了踉跄的脚步声。这一站开始,往后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们像雕像一样坐在位子上,过道里缓缓移动的人群,表情如送葬的队伍。
冬天回家乡帮族里亲戚守灵,几座粉刷过的房子如落魄旅人的脏衬衫,散落在不成气候的小溪边。三层的红砖房,没有装饰,砖块间的和泥保持着最初流淌出来的形状。前厅正中央的桌子上放着她大幅正方形遗照。黑色帽子,黑色衣服,中间一朵红色小花。照片一动不动的立着。他参加了这么多葬礼,脑中只有一个死人的模样。她下巴一颗黑痣,她也许给过他一颗糖,她的嗓子如这颗糖一样沙哑。在大堂后厅,用白绿相间的塑料布搭成小隔间摆棺材。小录音机在死人枕边念经,重复着庵里录下来的
“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摔了一跤,后脑破了一个洞。
南方的冬天,寒冷袭击着毫无准备的一切。红碳薄薄地披着一层热灰,烤着冬夜的守灵人。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抽泣声惊醒。她儿媳白发苍苍,双手交叉着,别在麻衣前,当哭到她所受到的苦时,人们开始安慰她,手伸向火炉。谈论封住了她的哭泣,把她从悲恸中拎出来,放入设计好、她情愿步骤中。她有福了,子孙满堂,安安静静、非常体面地上了青天,又有能力保佑活着的人。农村所有已经死去的老人,都在这样的祝福中死去。7点15分。唯有死人被原谅。昆丁,父亲说,给你这只表,不是为了让你记住时间,而是偶尔可以忘记时间。
7点……他握着手机伸向西装内侧的大口袋,松开五指,手机掉了下去,那口袋仿佛很深,一松手,什么都没有了……你会不会相信时间是静止的。我的脉搏是静止的。身体在空中是静止的。一个很深的地方……手机重重地落到口袋里……7点……他忘记看时间了。经常这样,把手机放回去后,才意识到什么都没看到。
守灵夜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他们会被领到台前站着。黄师穿着黑色袍子,整个寒冷夜晚的大部分时间,站着一动不动。经文随着他右手的铃当有节奏地摇晃,平稳地滑向袍子一样黑的深渊。在夜晚八九点钟,乡亲很多,黄师的声音也最响亮,房子仿佛被欢笑的灯光、角落里堆满带点欢庆色彩的丧货,被众人的嬉笑和脚步填满。十二点一过,该走的都走了。房子寂静下来,一动不动在蹲在夜色里。灯光冷冷地洒在红色赤裸的砖块间,响亮的摇铃声清脆地打在夜最明亮的部位,经文仿佛从她被覆盖的躯体上流过,整个柔和地、温暖地罩住她。他们从台前回到后厅的遗体间,开始折叠纸钱。她的孙女用木棍捣弄燃烧的纸钱内部,火舌舔着飞起来的、中间布满小窟窿的灰烬。它们乱舞着,从火的外圈,慢慢地落下来。
【特邀评论】
邱雷评《桥》
我读这篇小说时的一些想法,已经在论坛的跟帖里说到了,重读一次感觉也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现在把跟帖里提到的问题再说细一点,希望能对更具体地重视这个问题起到一点作用:
以观念聚集,或者以观念的形体构成的材料,在深思熟虑又有整体性的把握的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甚至不止是“大气”,“大气”对一类小说来讲还只是静止的、视觉听觉上的愉悦,是一种被动的“显现”,而且过分强调这个有时会导致对这些材料表面所发出的瞬间光彩的过度沉迷,也许就忘记了,或者是偏离了可以更好地动用它们的叙述轨迹。实际上更应该重视的是它有内在的磅礴之力,这种力量可以超出它的外观形态,更持久地发生影响;具备这样的力量也使它可以提升更高层次的统一之美,可以有万千气象又不失连贯和一致;既坚定硬朗,又势如穹窿。
既有这样广远的宏景,在对待每个词、每个句子、细节的时候,仅仅“雕琢”就会显得不够,“雕琢”更像是不触及材料内部,只在借形塑形、因势造势,以这种方式也许只做到“各显其美”就很难再进一步了,因为它看待这一个个词语、句子的方式还是孤立的,只能使它们彼此相间做得好可能势均力敌,做不好也许就有明显落差,参差不齐以致相互牵掣。笼统地讨论怎么统领这些材料有点奢谈的意味,不过有些极朴素的观念应该能够作为共识的:既然这些观念都从生活中来,这些词语、句子,也都是生活的发现与发明,那悬空起来考校词句还不如把它们再放回生活,置于最初产生它们的景象和气息中,可以更容易体味到一些在小说中看起来也许极微小的差别的现实意义。
这同样也要求写作者认真地对引征的素材加以辨别,一方面是区分它在其所出之处和它被引征之处的意义不同,表面上看这个要求是每个作者都能考虑到、都会谨慎对待的,但真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引征时的需要与被引其时的需要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视为一致的时候,这种差别就不容易被发现了。另一个方面则主要是考虑到作者何以会引征的出发点,是最基本地在生活中,在自己的写作中重新发现被引征的材料的重要性;还是仅只策略性地想对被引征的材料进行再度的加工以赋予它另一层面上的价值,这个区别更为重要,忽视它容易在小说里造成更深度的含混。
因为我也很喜欢这种挖掘观念、重塑观念的素材,能比较容易理解动用这种素材的写作包含的精神动力,也清楚这些作者绝不会满足于观念在小说中的抽象性、引导性的作用,而往往更希望它们能够调动作品的各个要素为一体,使其饱满丰厚。这样的小说,向好的方向看有穆奇尔,向不太好的方向看有昆德拉,都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