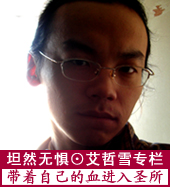这篇文章的开头本来是这样的:
毫不惊讶地发现,只要我肯以“倒霉”或是带有类似含义的关键词开始一段对话,立刻就会有糟糕的事情们以难以招架的频率袭来。可以预见“安慰”必然会在对技巧性的执着追求中成为一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学问--因为有太多的遭遇表明:我们试图去安慰和寻求安慰的行为,往往是以一颗高烧四十度的头颅贴上一颗烧到三十九度九的头颅寻求降温而告终的。
我本来想接着说:这意味着什么什么很糟,什么什么可能是指生活,也可能是指生活的环境,也可能是环境的某一部分……但这最终作罢了。因为直到12号下午,我只完成了一个开头。
然后,不能使用那些被日常生活冲淡了色彩的词汇进行谈论的事情发生了。一场灾难,一场空前接近我们生活的灾难以大片废墟的姿态出现在了熟悉的土地上,所带来的只有破坏和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死去,更多的人失去了生命以外的重要东西--这种时候,悲惨沉重的遭遇已经无法让人在比较行为中分享到被安慰的愉悦了。
多少人的死亡、多少珍贵事物的丧失才能算是一场真正沉重、沉重到必须诉诸于相互抱怨以外的行为才能获得慰藉的灾难?非要有一个具体的五位数字才能使人深深叹息?
与自然灾害相比显得无比细微的苦难时刻弥漫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这困难虽然细微,却并非不值一提,尽管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选择忽视它们:一团欲望状的生命总在满足时的无聊和不满所招至的空虚之间徘徊。凝视悲观的代价是失去生活,所以对这些苦难不闻不问是明智的选择--但是最好不要因此忘记了我们的处境:我们是苦难班的孩子们,在任何一种糟糕的处境中,我们都同在一起。
所以,尽可能不要成为他人的苦难,不要带着恶毒或不平衡的心态为他人带来苦难。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更大的灾害背景前,当我们行走自己的舞台上时,总是需要,并应当给予彼此安慰。
还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段子,但它们不适合更为残忍的五月。
上一次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兴奋地翻阅着儿童恐龙画册的小男孩身边,佯装对其不感兴趣却一直侧低着头试图给眼角的余光更广阔的视野来偷看那些用复杂线条描绘的陌生动物。
画册的内容足够丰富,小男孩过于快速的翻书速度并没有打乱我回忆的节奏。我几乎忘了自己在与他年龄相仿时也曾迷恋过那些,那些强悍、有力--会令任何一个男孩产生崇拜情绪的曾经的地表的主宰。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所能遭受到的苦难往往和我们同样幼稚,那些简单却没得到满足的欲望总是令人产生仅靠哭泣就可以消解的悲伤。后来,随着我们在世界上所形成的轮廓逐渐清晰,苦难的真实面貌也逐渐呈现于我们面前:我们如此真实地生活在它们里面,却不能拒绝将生活进行下去。因为和我们同在的还有种种不能割舍的珍贵和美好,或者仅仅是因为勇气,或者无可质疑、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望--无论是哪一种,无论哪一种是另一种的借口,我们总是要为活下去找一个隐藏得更为深刻,深刻到无须反复强调即可铭记于心的理由。
就连最死板的教科书也在告诉我们:恐龙那般强大的生物也会在真正的灾难中失去主宰的身份,总是在征服中以生命为标准获得胜利的惟有灾难本身。寻求和施与安慰是抗拒被苦难征服的唯一方式。消极的抵抗当然永远无法取得胜利,但是它足以让我们有勇气、爱--或者在这层掩饰下更为根本的欲望和意志,坚持生活下去,直到无法回避的尽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