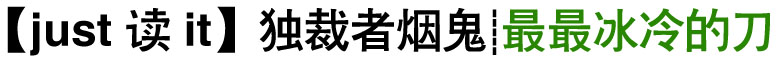我要写一篇书评,才发现最近两年内我从未完整的看完过一本书。这一事实让我稍稍恐慌。当然,书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真的不是。别听那些文化人的,丫都是骗子,他们都在计划写自己的书。
我最初读书是因为无聊,后来读书是因为习惯。像戒不掉的烟瘾。我成年后渐渐变得不善言谈,木讷。读书是我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一本书就是一个作家一个陌生人,或者老熟人好久没见长了小肚子有了抬头纹。有些人会觉得读书是一种霸道的交流方式,因为你只能听他说,却不能争辩,不能就他所说的事物与他进行讨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我必须选一本书,迅速的看完。不能太普通,不能太流行。那不够酷。于是我选了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这是我找死的开始。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一个敌视人类的作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欧洲好多评论里对他的冠名。1986年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伯恩哈德作为获奖者被邀致辞,这家伙上来就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东西,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文化部长当场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也纷纷退场。在之后的一些年里,重大文学奖项实在绕不开伯恩哈德,就将奖金和证书寄给他,而避免颁奖仪式。
2004年10月,以《钢琴女教师》一书名扬欧美文坛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耶利内克感慨地说,“如果伯恩哈德还活着,那该拿诺贝尔奖的是他,而不是我。”①
从1970年伯恩哈德获得德语文学的最高奖项“毕希纳文学奖”后,就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奖项。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伯恩哈德以绝对独立的人格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最后一部戏剧“《英雄广场》是为纪念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50周年而作,因对奥地利纳粹阴魂不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掀起轩然大波。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平民百姓,被伯恩哈德称为‘650万弱智’的奥地利人对他群起而攻之,他和他的剧作被看作是对奥地利人民的侮辱。”②伯恩哈德对此的反应是,立刻写了遗嘱,他所有已发表的或尚未发表的作品,在他去世后著作权规定的年限里,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我与奥地利国家毫无关系。我反对今后任何将我本人和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我死之后,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学性遗产,即信件和字条,一字不得再出版。”
这么有个性老头儿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倔”字形容了,你要和他交流吗?除非你吃不消化的东西噎着了,我就噎着了,非要找他聊聊。《历代大师》这本书由100多个短篇和两个长篇组成,短篇里最短的也就百十个字,长的几千字,两个长篇却都在十万字以上。短篇分成两个集合《声音模仿者》和《事件》,两个长篇分别是《历代大师》和《水泥地》。
实话说我都没读完。和这老家伙交流太困难,他从不给好脸子。我最初的交流经验十分糟糕,我看到的文字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小报记者发的连他自己都毫无兴趣的豆腐块消息。比如《害怕》是写一个能把一百五十公斤重的铁球举到两米高的泥瓦匠,因为害怕杀死了一个因姆斯特的学生,而被判终身监禁。《在利马》是写在利马一个衣着破烂不堪的男子被捕,他其实是出生于克恩腾州菲尔拉赫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向警察声称要去安第斯山寻找失踪的妻子。《太多了》写一个数十年具有所谓极高家庭意识的,颇受爱戴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将六个孩子中的四个杀死,他在法庭辩解时说,他突然感到孩子太多了。③《声音模仿者》写一个声音模仿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技演员。在帕拉维奇宫表演之后,又被邀请到卡伦山表演。可是卡伦山的人们有一些已经听过他在帕拉维奇宫的表演,所以要求他表演一些与帕拉维奇宫不同的表演,他也的确那样做了。可是当有人建议他模仿一下自己的声音时,他说,这个他办不到。《喜剧》写一个话剧院里的四个演员,因为剧作家们越来越乏味,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喜剧。但是自然的他们只会写他们自己,最后这部喜剧不得不叫《作者》。可是据报道,这部《作者》也没能给他们带来成功。
短篇几乎全是类似这样的文字。乍看上去,就像一篇篇写糟了的新闻消息。④虽然这样想对老头儿不太尊敬。但是我实在看不出这写东西有什么文学价值,难道还原到德语里去就成了唐诗?有一阵我决定放弃写这篇书评了。
然而有天上网,我回顾几则新闻,一则是关于俯卧撑⑤,一则是关于上海闸北分局⑥,一则是关于外国游客遇刺⑦。我突然醍醐灌顶:伯恩哈德,牛逼!他能将世界提炼到如此地步,我们的对死亡的冷漠、对病痛的恐惧、对政治、道德的怀疑,都洗练在他的文字里了。他的文字是一把冰冷的手术刀,不,这比喻太俗了,手术刀是治病的,而伯恩哈德是绝望的。他并不想救治,他知道,世界的病早已无药可医。他只是一把刀子,最最冰冷的刀子,将世界的毒瘤剖开,给我们每一个人看,想到这里我脖根儿发凉,不想再和这老家伙交流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⑧但是我又突然想起他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第一句发言:“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恍然大悟,原来这句话不是为了寒碜这些评奖,颁奖仪式的,而是要给我们希望,给我们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严肃的批判。
奥地利驻华大使博天豪先生在《习惯势力》北京首演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伯恩哈德“曾是一个不幸的人,在经历了不测命运的无数次打击后,他一生不仅同自身的问题抗争,同时也和奥地利官方对抗。他艺术地强调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消极面,因此也引发了许多对他的不满和批评。不可否认的是,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贡献在于,他把奥地利从舒适享受的生活中唤醒,使之开始进行富有价值的思考。而这恰恰是艺术的众多使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决定继续和这个老家伙交谈。我已经在进入他的两个长篇。我会把这一本书看完。在这里“严重”感谢一下这本书的翻译马文韬老师,他在译序里写到“关于翻译,伯恩哈德曾说过很难听的话,他说一本翻译的书‘与我写的书就不相干了,因为它是翻译它的那个人的书了。……一本翻译的书好似被汽车轧得残缺不全无法辨认的一具尸体。……一个人为什么要翻译呢?他自己写点什么不好吗?’……”马文韬颇有点无奈又有点无所谓的看待这席话。还是顶住了压力,一举将伯恩哈德推进汉语的镜子里。
烟鬼
2008年8月19日夜
①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9月7日王宏图《在音乐般的文字背后》
②引自北巫《伯恩哈德: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③小说原著和我用来介绍的文字几乎一样长短。
④伯恩哈德确实做过记者。
⑤瓮安“6.28”事件
⑥上海袭警事件
⑦美游客在京遇袭事件
⑧也许鲁迅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