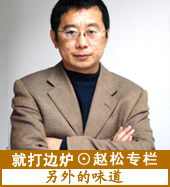关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有良史之才的极少,鲁迅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这种才能,固然可以通过《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作品得以体现,但同样也可以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这样的文章里看得清楚。如果说从前者里更多的可以看到鲁迅梳理、概括能力和文学眼光的话,那么从后者里则可以集中地看出他的非同寻常的洞察人的能力。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这篇鲁迅作品里少见的长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容、平和、宽容并且力求客观的鲁迅。比如他从后世评判起来最为复杂的曹操谈起。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曹操通常被称为“奸雄”。这种反历史的评判结果,在民间已经差不多成了定论。它首先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评判。简单的忠奸二分法,把曹操推到了反面。因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恰恰是不读史也不理会史的评价的。人们喜欢的是演义和演义里的评价。鲁迅的观点很简明:“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这话要是只有对照当时的环境背景,才能理解鲁迅的深意。鲁迅不只是肯定曹操的历史价值,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像当时他所身处的那样一个乱世,是很需要有曹操这样的人物出来的。
要理解历史及历史中的人物,就一定要懂得当时的社会背景,否则就会变成扯淡。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算新,但很重要。因为当时的很多文人,为了回避社会的矛盾现实,或躲入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路子里,鼓吹唯美或性灵,或不顾现实地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迈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里,都从不同的角度上制造了文学艺术的假象。鲁迅分析曹操“尚通脱”的原因,是为了扭转当时清流的固执。“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这评价之于曹操来说,古往今来并不多见。“胆子很大……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这种状态,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即使在鲁迅的时代,尽管有西学东渐,有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有社会的革命,这种“通脱”精神也仍旧还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人向来容易变得世故。同样是乱世,民国之初,与魏时相比,多的仍旧是拘束与顾忌。即使是现在,不是乱世了,中国的文人们仍旧有此特性,鲜有人敢把文章写得通脱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要在这篇文章里花这样多的笔墨肯定曹操的功绩的原因之所在。所以鲁迅可以称得上是曹操的后世知音。
而对于在尚通脱基础上走向华丽的曹丕,鲁迅也仍旧给予了肯定,并没有因为他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而加以否定,关键还是在于知道他有“尚通脱”的底子。“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里面曹氏父子的功劳最为显著。而对于同处在这个体系里的“建安七子”,鲁迅只是一带而过,但对于其中的代表人物孔融的处世观念却有相当明了的概括,虽然未及文章,但实际上也已触及到了根本。鲁迅的敏锐在于能准确地把握到那一时代文章风气转变的关键点。他对何晏的评价就是例子。引出何晏的目的在于谈及服药与发散,以及所谓的“名士派”。这里面并不谈文章,只谈一种风气。但明白了这种风气的特点,其实文章的源头及相关因素也就自然明白了。名士派的文章成就,最为充分的,还是体现在后面的“竹林七贤”那里,尤其是阮籍与嵇康。
鲁迅是非常欣赏这两个人物的,特别是嵇康,他还曾亲自花时间重新校订过《嵇康集》。在分析这两位人物的时候,鲁迅还是注重于分析他们的观念、行为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样的洞察力,不要说文学家里不多见,即便是史学家里,也是第一流的。理解了这一层意思,对于看懂那时的文人及文章,是大有助益的。具体到阮、嵇二人那里,则同样是说到了骨子里:“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而后世之人之所以常常会误解这些前人,原因也就在于他们不能看破这一层,只能去浮妄地猜测那些表面文章与行径了,这样一来,就岂止是“不懂”二字可以了得的了。
对于文学史上更为重要的陶渊明,鲁迅的分析也是着力于纠正以往的一些误解与错觉。“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这里所说的“别一种看法”,其实也就是这整篇文章所蕴含的那种研究方法。看不清那个时代,也就看不明白那个时代的人,进而也就更难看懂那个时代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展示了他是如何看懂一个时代的风气之所以然的,他是如何看懂那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也展示了他的研究方法,这对于试图写下文学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思索的事。同样,对于后来的读者该如何去读那些先辈文章,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启发。
2008年9月20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