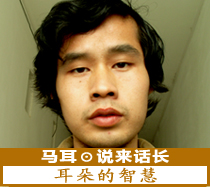最近黑蓝小说的创作呈现疲软状态,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没有好的小说,甚至没有一篇称得上是有点意思的小说,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沮丧。
这种状态,如果从个人的处境来分析,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原因。以我自己来说,自从六月末以来,基本上就没有好好地写过东西,除了必要的杂事花去的时间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被一种无谓的激动耗费了,一些事情在发生着,虽然在远处,但却不能不让人心潮澎湃,使人静不下心来从事那比较冷清的写作——有一个盛会即将开始了,但从我的视角来看,这不是好的盛会,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了它而变得过于紧张,光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不是一个好的盛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盛会已经是一个失败,因为伴随着这个盛会上演的,是一连串的戏剧,参与者小心翼翼,不想给任何人留下把柄,维护者声嘶力竭,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挥舞,反对者阴阳怪气,做出种种下流动作……盛会本身不再重要,倒是与之相联的种种枝节不断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事情发生了,就不再会消失,而是像一块块礁石,留在人们的心中,让他们在某个黑暗的时刻摔倒在地,或者在另一个危急的时刻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稻草。我们观察一颗石子在水面上形成的涟漪,看见它一圈一圈永无止境地向外扩展,就会知道每一颗石子都在构成着一个湖泊,从那一刻起,那个湖泊就成了那颗石子的湖泊,千万颗石子沉睡在湖底,其中的每一颗都曾在某一刻拥有过这个湖泊,并从那一刻起继续拥有着这个湖泊,尽管湖泊本身在不停地改变。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成了一出庞大的戏剧中的角色,而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想要在这出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真正有心思坐下认认真真观赏这出戏剧的人却寥寥无几。
或许有些戏剧本身就不是用来观赏的,它的存在本身就像一个黑洞,一切离它太近的人都被吸入其中,因此就连那寥寥无几的观众也只是这出戏剧的一个角色,它在制造一种幻象,证明这出戏剧仍然是一出戏剧,仿佛一个积满石子的湖泊中的最后一条鱼,在努力证明这个湖泊仍然是一个湖泊。这出戏剧发生得离我们太近,因此它注定要成为一个黑洞,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吸入其中。有谁看过一出极为庞大的,以整个世界为背景的戏剧呢?如果他看过,那他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演员,让演员来叙述这出戏剧是极不可靠的,他早已被纷繁变化的情节迷惑了眼睛,失却了一颗沉静的内心,而没有沉静的内心,他拿什么来叙述这出戏剧呢?
以上所述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的个人处境。我不得不说,这样的处境很不利于写作,我已经成了一个演员,而人不可能一边作演员一边去写作。其实除我之外,有很多人也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认为这种处境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状态到底会持续多久,并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写作?
唐代的陈子昂,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初到京城长安时,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卖胡琴,标价百万,周围人群议论纷纷,不知真假,都不敢购买。陈子昂上前去,连声称赞这是一把好琴,当场用重金买下,并宣称要在第二天邀请众人听他弹奏此琴。到了第二天,陈子昂在一个广场上摆满酒食,邀请众人享用完毕后,捧起胡琴,说:我陈子昂满腹诗书,可惜无人识才,这把胡琴,不过是一把下三烂的乐器罢了,留着它有什么用?说完了,举起胡琴就砸了个稀巴烂。
陈子昂的这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不过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故事本身。从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来看,陈子昂是成了名,他把价值百万的胡琴砸了,吸引了众人的眼球,然后当场把自己写的诗文赠送给现场来宾,结果在京城一举成名。叫我说,陈子昂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杰出的演员,他关于胡琴的一切,都是在演戏。然而演戏不演戏,其实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砸了胡琴,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事。在他砸胡琴之前,他还是一个演员,在一出戏剧里扮演角色欺骗观众,等到他砸了胡琴,他就变成了一个诗人,他之前所做的一切行为也就从一个自欺欺人的欺骗变成了一个诗人的自我推销,他用一把砸碎的胡琴拯救了自己。
由此看来,即使面临的是一个黑洞,我们也仍然能够拯救自己,只要我们能够砸碎一件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粉碎声让人们猛然醒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写作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一场毫无边际的戏剧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观众,而不是一个假扮观众的演员。
但我们的悲剧恰恰就在于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砸。我们从前的许多写作者,他们砸碎了很多东西,于是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名声,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砸碎什么东西,而只是进行了一场砸碎东西的行为艺术表演,他们不但没有砸碎东西,反而把这些东西变得更为坚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面临的困难就是,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可砸,所有的容易砸碎的东西都在从前的行为艺术表演中被砸碎了,只剩下一些坚不可摧的,被一代代的演员塑造得越来越坚固的物体。从前的那些老家伙,凭借着他们砸碎东西的虚假名声,现在正坐在戏场的中央,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后来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砸过什么东西,他们也因此不希望别人砸任何东西,他们一直都是一个演员,他们在一出无边的戏剧中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实际上他们只是一堆狗屎,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后来者仍然都是狗屎,一个狗屎的世界比一个诗人的世界要好得多,他们说,因为在狗屎的世界里,你能够变成任何东西,而在一个诗人的世界里,你只能是一个诗人。
于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点像莫泊桑笔下的图瓦老爹。图瓦老爹是个爱酿酒,爱喝酒,也爱开玩笑的男人,他用他的笑话砸碎东西,虽然不是一切东西,但起码是一些东西。偏偏他的老婆是一个极端古板的人,她最大的爱好是养鸡,当然也就不喜欢开玩笑,而且她也极度讨厌图瓦老爹,总盼望着有什么坏事发生在他身上。这件坏事还真的发生了,图瓦老爹得了中风,瘫痪了,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酿酒、喝酒、开玩笑了,然而他依旧很开心(有些人就是那样,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他们总是很开心,这种性格其实更接近于一种天赋,拥有它的人比没有它的人要活得轻松得多)。图瓦老爹的老婆却因此不高兴了,她因为他的开心而不高兴(这种性格,在我看来,也接近于天赋,很少有哪种后天的影响会顽固到抗拒快乐的程度),她使用一切手段试图削减他的快乐,但并不成功(两种互相对立的天赋发生矛盾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战胜另一方,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发生转化,最多只能通过某种手段让一种天赋控制另一种天赋)。最后,图瓦老爹的一位朋友对她说的一句玩笑话给了她启发,她给了他十个鸡蛋,要求他躺在床上给她孵蛋,图瓦老爹当然不喜欢孵蛋,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任务,当十只小鸡从他的胳膊底下唧唧出世时,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图瓦老爹最后的喜悦是一种被劫持的喜悦,当他在床上纹丝不动、屏神静地孵着鸡蛋的同时,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只老母鸡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这只老母鸡如果被赋予拟人化的角色的话,就是一个嘲讽者,就是一个不爱开玩笑的人对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的嘲讽,不幸的是,这样的嘲讽和现实生活的逻辑是相吻合的:不爱开玩笑的,不喜欢把东西打破的人会取得胜利,成为那些爱开玩笑的,爱打破陈规的人的控制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写作者,我们蜷缩在一个个阴暗无人的角落进行创作,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我们也不会去娶一个要求我们孵蛋的老婆,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控制者的影子仍然是无所不在的,它飘荡在我们的身边,在餐馆里、发廊里、剧院里,甚至在我们的心里。本质上,我们全都渴望控制,控制他人或者被他人控制,这是一种美妙的感受,最性感的舞蹈总是由戴着镣铐的人跳出来的,他们衣衫褴褛,却又绝不至于衣不遮体,那些一点点、一片片、一块块、一条条衣物的破碎恰到好处地实现了视觉上的封锁与挑逗,破碎处隐隐露出的雪白肉体和镣铐的铛啷响声足以让寡闻薄识的观众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高潮。控制的本义就是阻止毁灭的冲动,老婆们,在家庭建立起来之后,就倾向于成为一个控制者,以避免这个精心构筑的窠臼被鲁莽而喜新厌旧的丈夫们毁坏。世界上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却有很多个多托尔斯泰夫人式的老婆,正是她们毁了身边的托尔斯泰。从推进文学的角度来说,所有温柔贤惠的老婆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放荡不羁的情人。而除了老婆们温柔的束缚外,更多的束缚来自于家庭之外,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污浊空气里漂浮着的种种有害分子。很难分辨出到底是谁最先制造出了它们,它们在我们出生时就已存在,以致于和空气本身一样不为人知,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的血液。当乐声响起时,我们的双脚总会情不自禁地蠢蠢欲动。毒素发作了,舞蹈的冲动被熟悉的乐声唤醒,奴才的嘴脸在这一瞬间暴露得淋漓尽致,哪怕镣铐并不曾套在我们的脚踝。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场盛会上来,那场盛会即将开始了,如同我们以上所说的那样,它就是一场戏剧,它不试图砸碎任何东西,也许在它的节目单里,有一个砸碎胡琴的表演,但是被砸碎的只是一把胡琴的塑料模型,并不是一把真正的胡琴,真正的胡琴已经被他们锁了起来,用十二层保险箱守卫着。我越看越觉得这是一场古怪的盛会,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场无休止的戏剧中来,这多人,毫无激情,却还在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规定动作。对这一切,唯一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的一生都在演戏之中,因此这一场戏剧对他们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人生如梦,万事皆空,古人说得很好,人生不过是一个悠长的梦魇,每个人不过是戏台上的一个戏子,砸碎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当我费尽千苦,好不容易找一把破旧的吉他,准备一下将它砸碎时,几个警察就围了上来:“你干什么?不准砸东西!”我明白,他们并不是警察,他们只不过是几个戏子,他们又的确是警察,因为他们可以阻止我砸掉那把破旧的吉他。
由此看来,目前的戏台上有两类地位显赫的角色,一类是貌似砸过东西的老家伙,一类是不准别人砸东西的警察,老家伙们喜欢四处宣扬自己当年砸东西时的丰功伟绩,实际上他并不喜欢砸东西,更不喜欢别人去砸东西。警察则像图瓦老爹的老婆那样,忠心耿耿地看护着他们的鸡蛋,生怕有人把它们给压碎了。这两类人正在共同维护着正在上演的这出戏剧的秩序,他们都是其中的戏子,并希望别人也投入其中,无论怎样,赞同还是反对,只要一投入其中,他们就能有所获益。这两类人越强大,我们的写作就越疲软,处境也越发的凄凉,这一场戏剧的结束也越发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