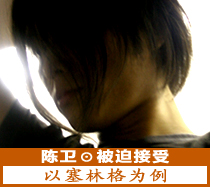一种让人竞相模仿、并且在模仿时还感到自己是在独创、而同时别人却能在这些模仿里看到其源头的风格,最终将因为这些模仿而损耗这种风格的魅力,甚至这些模仿将成为质疑这种风格的主要起源。
正过来说,最有魅力的风格,不可能激起别的作者以这种风格的主要特征进行大规模模仿;别人从这种风格里吸取的是营养,这些受惠越不易察觉越足以证明这种风格的宽广、深厚和隽永。
于是我们看到,有的风格始终吸引的是它的同类,受惠者以一目了然的模仿为标志,就像药品针对着相关的病人;而有的风格除了吸引它的同类之外还能吸引它的异类,与它的一些特征相反的悖逆者也不会对它反感,甚至也隐秘地从中吸取营养。
这种能够吸引异类的风格,往往不具备它所处时代的最大个性。个性实际上正是病症本身:它反常、夺目而容易传染。在个性张扬的时代,要做到没有个性,则需要强大的免疫力。而要做到没有个性之后的个性,所需的正是形成风格的整个过程。
正如塞林格的小说没有刻意藏匿的视角,没有结构复杂、拗口难懂的长句,没有幻象、隐喻或者象征,没有意识流,没有沉迷已久的腔调,没有泛滥的个人主义,没有过于时髦、颓废、亢奋、足以改变一代新人的新词汇和生活方式,不刻意聚集“小人物”,不“朴素”,不荒诞,不异化,但是想必罗伯—格利耶或者卡夫卡也不会反感塞林格的小说。
在整个现代主义泛滥的二十世纪,无论从小说文体,还是技法革新,或者世界观、价值观来看,塞林格似乎都只能划入“传统”或“古典”作家,但是当我们用“传统”或“古典”指称他的时候似乎舌头会打个结。他既不“现代”,也不“古典”,他只是塞林格。
剔除身处时代先声夺人刺人耳目的特征之后,依然形成引人入胜的风格,也许这就需要“中正”。在最高最大的点和面上,“中正”和光同尘形同素人,而事先的剔除和抑制获得迂回以及风格所需的细节的充实;后者考验出在品质上而非外形上钻石般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