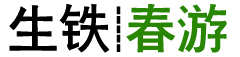每个季节都有那么几天特别清爽的日子,或者艳阳高照(风吹过老杨树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或者秋风萧瑟(国槐的黄色叶片纷纷飘落在柏油路上)……但带给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安详,释然,使人依稀找回一点童年时代跟着老师同学一起外出春游时的气味。
说到春天,每年清明时,我们全家都要去给爷爷扫墓。所谓全家,就是我,还有我爸、我妈。
每一年都去,每一年都拍照片,回到北京的这二十年来,这件事在我心灵里的印象,也由一种肃穆、紧张、陌生渐渐变为半是温存半是惆怅的怀旧。
以前是坐公交车去,一大早先从西便门坐市区公共车到动物园终点站,再从动物园的郊区巴士起点站坐车到西郊的某一站,下车还要走上10分钟,才能到那个叫“万安公墓”的墓园。再后来是开自己的车去,一辆大众牌的POLO轿车,那是03年闹非典时我爸买的。后来我爸又换了辆铃木的JIMNY两门吉普。我们现在扫墓,就开车走西四环高速,从四海桥左转,走北坞村路,再左转上闵庄路,到旱河路路口就到了,以前扫一次墓要一天时间,现在不过两、三个小时。
我爸十岁前家里有一辆菲亚特轿车,皮座椅,绒面内饰。再之前是辆福特。现在家里还有他幼年时坐在车里拍的黑白照片。后来的大半生,我爸都没再有过自己的车。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很喜欢车。
墓园对面有一大片桃树林,那个季节正好开满桃花,桃花那喜嫣嫣的粉红色,却一点没有艳俗的味道,衬托出远处的玉泉山和山上的玉峰塔——只有它们在我的印象里是从没变过样的。以前看到这片桃林,就知道万安公墓快到了。这二十年来,墓园陆续修缮了几次,把本来散乱无章的墓地划分成了一块块区域。我爷爷的那块墓地在金区赭组。
但每次去看爷爷前,首先要看我的“太婆”,也就是我爷爷的母亲。她是江苏吴县人,却葬在北京,这是我爷爷的安排。
我们把刚买的两束花都摆到太婆的碑前,鞠三个躬,然后照两张照片,留下一束花,带上另一束,去爷爷那里。在我有印象的这二十年来,爸爸每到此刻总要说相同的话,“你爷爷和你太婆最好。爷爷对他妈妈最孝顺。我们来看太婆,爷爷也高兴。”
“您见过太婆么?”我想我大概有五、六次都是自然地问起这个问题。
“没有。”我爸说。
我也没见过我爷爷。我爷爷是西医,受他影响我爸也干了这一行,干这行不求人。在我爸还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就已去世。爸爸是小儿子,和爷爷差40岁,所以深受我爷爷宠爱。我爸受我爷爷的影响那么深,以致于影响到了我。家里每遇到好事,我爸就说是我爷爷在冥冥中暗助我们——大到我找到一份工作、结婚,小到我爸外出会诊时所得到的一些诊费。扫墓那天总是个好天气。即便早上醒来时还阴云蔽日,到路上的时候也必见了晴,从没一次下过雨。我爸就说:“爷爷又给了咱们一个好天……”
每次我们穿过墓园去给爷爷扫墓时,免不了在沿途看到一些他人的墓碑。有的显然已荒废多年,碑上镶的烤磁照片里的人脸也被人砸碎,也有的可以看出每年都有人清扫。老的墓碑各有不同的造型——方尖碑、十字碑,还有立着石狮子、做成牌楼样的。碑文里也各有内容,不像新碑,都是一样规格,一样模式,好象士兵站队列,拥挤、促狭、毫无个性可言。有一对夫妇的和葬墓,碑上镶着夫妻两人新婚时的合影。男的是位外国人,碑后面刻着几个大字“生无离,死无别。”还有一个年轻人的碑,也有主人的照片:梳着带波浪的分头、鬓角挺长,眼神分明充满朝气(和我显然不是同一类人)。他的碑挺高,但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1963~1989)。这么多年来,我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些墓碑的主人也成了我的老朋友——他们活着时与我无缘,死后却每年得见一面——对这些感
触,十几年来我一直有心把它好好写一写,但从没有动过笔。随着年纪的增长,在墓园里行走的感觉也是不同的,小时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现在则要复杂得多。多活些年,或少活些年,在这个环境里看来,只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
墓园老区的环境多年来没有太大的人为变动,柏树参天,能听到在北京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各类鸟鸣,爸爸也照例要说:“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喜欢万安公墓,说死后要把他葬在这里。”
奶奶也和爷爷葬在一起,算起来她离开人间也有十几年了,但我回忆起来却好象还是前两年的事。自从爷爷去世,父亲一家也就渐渐没落。60年代末,父亲一家人彻底丧失了一切,包括自己在北京的家。按爸爸的话说,“从爷爷去世,奶奶就没再享过什么福。”奶奶比爷爷多活了30年,我们一家和她一起生活过将近十年,直到为她送终。
爷爷的墓地有个九尺见方的水泥围栏,四角种着树。这是80年代初我父亲和他的哥哥姐姐一起凑钱重修的,再晚两年,恐怕连旧碑座也要找不到了。到了这里,爸爸照例坐在墓床的一角,从带来的塑料袋里拿出啤酒、可乐和烟,摆在爷爷的碑前。他自己点着一根烟,然后又拿出两根给我,让我埋在右角的树根下,“给爷爷两根好烟抽。”他说。我和我妈擦擦墓碑,扫一扫墓碑附近的落叶,然后我们一起鞠躬,默哀短短的几秒。我爸打开啤酒罐,我们两个人每人喝一些,然后把剩下的洒在墓栏边的草丛里。“爷爷奶奶都喜欢喝啤酒。”他说。在以前交通不便时,到这里往往已临近中午,我们还会拿出随身带的面包来吃,就像春游时那样。
每次当与爷爷告别时,我和妈妈已经走出十几步远了,我爸仍会独自在爷爷的墓碑前静立一会儿。我不知道那时他在想什么——但我能想象出他会想些什么。我爸比我高,比我魁梧,我长得更像我妈妈。他的头发总是一尘不染向后梳着,他有着医生式的白皙皮肤,长方型的脸膛、笔直的鼻梁和紧抿着的薄薄的嘴唇都好象彰显着他那作为男人的意志力。
在班驳的树影里,爸爸穿着长长的风衣默然站立在爷爷墓地前的样子,长久以来成为我内心中某种说不清的象征。我从没见过一个儿子,像他那么深爱自己的父亲。
他常和我讲起的有关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快乐回忆,有多一半都是与我爷爷有关的。每当他买到一块新手表,或者看到什么新的数码产品,或者在逛乐器店时,他都会提到我爷爷,他会说如果他还在的话,他也一定会喜欢的。
在回家的路上都是我在开车。我爸他免不了要在车上打盹。每当我发现他在打盹,就总忍不住扭过头去看他。我看到一个男人因无法战胜年龄而变得越发厚重的眼皮、越来越松弛的下颌皮肤和那依然紧绷着的,但两端却开始下垂的嘴角。在他变色眼镜镜片的上缘,可以看到他微微皱着的眉头,那使他在沉睡时仍威严不减……但却也更显得疲惫有加。
我的内心深处是如此不情愿、但又如此忍不住不停地扭头看我身边的这位老人,看着他的头慢慢垂下去,又突然抬起来,无论是电台里的音乐声,还是我和我妈的闲聊,都不能干扰他与睡魔的这种专心抗争。有时,过不了一会儿,他又醒过来,表情不再严峻(反而有些茫然),并很自如地加入到我和我妈的闲谈当中。
在今年清明的扫墓归途中,正在打盹的父亲突然抬起头,他说:“汪铁你看,是飞碟!”我才看到在他那一侧的车窗外,有一架与我们平行的、无声飞翔着的飞碟。它的直径和一辆集装箱卡车差不多长。它突然向我们慢慢靠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爸就大声喊:“快起飞!”他把手伸到我的方向盘下方,拉了一下JIMNY的制动杆,JIMNY颤抖了一下,就飞向了天空。这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飞碟刚好移动到我们刚才的车道上,而在它身后,已经是一片火海。高架桥被炸断的碎片和一些烧着了的汽车正从半空里掉向地面。
我被吓出了一身汗,车还在向半空里攀升。我爸一边叮嘱坐在后座的我妈系好安全带,一边在自己的座位下胡乱地摸索着什么。很快他掏出一支折叠枪。他勒令我往回开,让我驾驶JIMNY绕着飞碟转,“开稳了!保持距离!”他一边喊一边打开他那一侧的车窗,以我想象不到的灵活把头和肩膀伸出车窗外,端枪瞄准,枪口正对着那突袭人类的外星飞碟。
【特邀评论】
shep|骑士远征——关于《春游》的一次曲解
吉诃德独自上路的时候,恰是炎炎七月的一个清晨。当时,天还没亮,四下也没有一个人。但对曼查的骑士来说,此乃初展宏图、征险除暴的好兆头。“他竟不觉心花怒放”。
这是多么让人惊异的事啊。但,正是从这里开始,《堂吉诃德》便具有了胜过一切文学的“某个闪光点”。同时,作为主人公的吉诃德也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一般“冒险力量”的禀赋。在这个天还没亮的七月早上,曼查骑士在谵妄中、在痴醉状态下,毅然决然地推开了世界的隐秘大门——一个应当永远记住的时刻——随着这道门的被打开,吉哈纳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家铁锅里的那些牛肉,都被迫从主宰的位置上引退了下来。这点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将小说文体推到了一个令其颇为尴尬的境地里:小说现实,是否全部源自于生活本身?
基于同样的追问,《春游》也不得不为自己作答:小说现实并非全部来自于生活,不,小说终将会走向生活的反面。因为,这不仅仅是小说的内在需要,更是生活本身对自己评价的否定性回应。
生活从不严苛地对待自己。恰恰相反,生活是她自己的嘲弄者。于是,老人才喊出了“飞碟”两字。而这个飞碟的出现就和吉诃德一次征险的开头一样,马上就逼退了重重的散文雾障。是的,浓云一般的散文雾障塞满了这篇不长的小说的字里行间,直至不明飞行物的降临为止。可,出现在结尾处的飞碟却又如此地顺理成章,以至于它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之前的感慨和抒情,完全就是为了给这最后出现的荒诞场景作铺垫而已。
难道,散文部分真的只是结尾的陪衬和垫脚石吗?未必如此。它除了作为打开秘密大门必备的敲门砖外,仍然存在着重要价值。曼查骑士奇妙旅程的每一步,不就是踩在生活铺就的道路上的么。他结结实实地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和由此展开的每一个真实景别的支点上。也正因为此,吉诃德才没有置身于虚无飘渺的云端。至于《春游》给人的那种错觉,则是作者意图的具体体现。
嘲弄自身的生活,即等于小说。或者说,作为彼此成为反面的生活与小说,从始至终都是处在一个曼妙的矛盾体系之内的。在这一体系内,现实与超现实;平淡无奇与如梦似幻,统统脱离了原本的约束,汇流为一道色彩斑斓的火焰之河……这适用于小说,当然,这同样也适用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