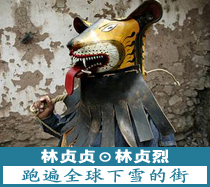(↑ 以上是旅行记录的封面,是一个长腿女人的影子。她最近和安吉丽娜·朱莉一样,瘦得要命。)
珍珍的不完全旅行记录
(↑ 以上黑色粗体字的部分是标题)
因为从没认真地转过谁家的街,而且每个地方只选一张图片,所以这份旅行记录被称为不完全。每张照片都是一首短小的叙事诗,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女孩,她为了生活放弃了理想(宅在家里玩儿一辈子的生化危机),之后离乡又背井啊,孤苦又伶仃……
(↑ 以上深红色的部分是牢骚满腹的题注)
(↓ 以下是文章的正文)

↑ 以上这张图片是08年南非开普敦。天边有一座白色的灯塔。我在车里被海风吹得够呛。
这幅照片表达了很多意思,抽象来说呢,就是思念——
对灯塔以北全世界所有PS3以及拥有着PS3的温暖房间的思念。

↑ 以上这张图片是08年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在博物馆外的小冰雨里走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了这家位置蹩脚的博物馆。这进了博物馆之后又热得不行,又没零钱去存大衣。
整座大英博物馆里,就属礼品店里的人最多。
这幅照片表达的意思也非常多。抽象来说就是某种仪式。很多缺胳膊少腿的塑像在为丢失了使用PS3手柄的能力而感到哀伤,哀伤写满了他们残肢背后的墙。

↑ 以上这张图片是08年在马耳他群岛。到达的时候正赶上日落,好不容易不冷了,又在山里迷了路。转过一个山坳,眼前就是这幅破破败败的日落。后来被酒店的门房大叔嘲笑,说我们马耳他自古就这一条路,这样你都能迷路云云。我回答说你们家的地图上又没有存盘点,这样的地图怎么能被生产制造出来云云。
这幅照片想表达的意思也非常多,抽象来说就是文明尽头的破败。这世界上除了一窝蜂的游客和考古学家,没什么人再能想起这座亚特兰蒂斯城的遗迹。

↑ 以上这张图片是09年春天重归马耳他群岛,去了古时的防御工事Mdina。在很多的土炮楼子之中,有这样一个精致的盒子挂在一家礼品店的门口。
仍然是很大很冷的山风。古城即将关闭,礼品店里面的人仍然很多。
这张图片所表达出的意思是叙事时绝对的威严与教养。无论在礼品店门口还是在古城的石门上,纹章掩盖了木制的纹理,一如既往显得那么的优雅。

↑ 以上这张图片是08年冬天在莫斯科。斯大林时期建造的、砖石混凝土结构的、集成电路板一般的公民宿舍楼,跟北京三环路上的诸多民房建筑有一拼。他们是如此公然地存在于城市之中,佯装秩序与和平,以至于积雪也没办法掩盖其狰狞的丑态。
这张照片的想表达的意思是控诉和责问,以及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与贫穷。

↑ 以上这张照片是08年秋天在悉尼。与照片上的风景相对的角度是悉尼歌剧院,灯海相映的感觉的确很浪漫。这张照片主要想表达的是那个球形的路灯替代了月亮的主题。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盏灯,至今没有一盏是我的。
坐在港口上的酒吧边上抽烟,因为丢了相机而闷闷不乐,发誓这辈子都再也不买相机了,就一直用手机拍照自暴自弃算了。不过酒吧里的DJ心情不错的样子,放了The
Cure乐队的《Love Song》和Cyndi
Lauper的《Shine》。
酒店失物招领处的大叔说得一点也没错,有些东西丢了之后,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找不回来。

↑ 以上这张照片是08年秋天在悉尼海洋馆。这张颇具舞台效果的图片描写的情景是海洋中的某种别人知道名字而我却不知道名字的未知生物在管状的物体中露出了半个头,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它露出头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惊恐。
海底深处的生物,总让我想起江户川乱步的《人间奇形》。它们陷得那么深,那么黑那么冷,但却那么真实而坚强地存在。

↑ 以上这张照片是09年8月份在广州。图片上的破楼是陈家祠背后的一栋居民楼。空调的存在表示楼里面确实有人居住,而且还想在楼里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在大连海边也见过一幢类似的破楼,门口有两三个蒙着彩色面巾的男人,赤裸着上身,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这幅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误解和家庭。

↑ 以上这张照片是在09年春天的迪拜海边。去沙漠里的希尔顿酒店做SPA,出门之后就是这片荒凉的近乎荒唐的海岸线。黄沙大漠与碧海蓝天共存,说起来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海水温湿咸涩,海盐有助于美化人类丑陋的、布满了毛发的皮肤。另外盛夏无敌。和冬天相比,我果然还是喜欢夏天。不管哪儿的夏天都好。在海边一边听PSP里林小花同学的《Foever
Love》一边晒太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成为天龙好呢还是成为地龙好呢?这时候一个黑袍的阿拉伯大婶走了过来,提醒我斋月就要近了,不要四处得瑟穿着比基尼乱跑。
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有信仰就是NB啊,不用担心成为天龙还是地龙的问题,一辈子都不用晒太阳。

↑ 以上这张照片是08年4月份在神户。阪神地震的重建之后,神户港口被圈起来一块,里面有被海啸虐碎的地面和歪七扭八的路灯。神户港那天的光线特别好,几乎好到照片上要暗。这种光线让我想起大友克洋和他的《蒸汽男孩》,那艘悬挂着万国国旗的蒸气船缓缓驶入港口的情景。
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创伤和创伤过后不断舔舐伤口的心理。

↑ 这张照片是09年4月份在京都清水寺。我小时候家里有套拼图,画的就是这样的情景。他们都说我去京都是为了4.17FF7蓝光完全版发行或者去买克劳德骑着摩托车的手办,其实我不过是为了套拼图而已。
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樱花这种东西,虽然建国门地铁站门口也有,但还是在京都这种地方看起来比较美。

↑ 以上这张照片是09年夏天在德国科隆。德国人的习惯是在有水的地方搭凉棚,然后再凉棚下喝啤酒吃香肠。科隆大教堂背后的草地上,几个女孩在玩儿天使与魔鬼的游戏。他们招手叫我一起玩,我却不知道自己该当天使还是魔鬼才好。
后来那个打扮成天使的女孩对我说,没关系,我正好多了双翅膀,给你。
我顿时想起《Boy
A》中那个小女孩画的画。这是你的刀,这是你的翅膀。
这幅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世事无分对错,全在于选择而已。

↑ 以上这张照片是09年8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日出的时候,窗外缓缓驶过一个红色的热气球,一幅堂而皇之的样子。我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它忽然喷了两下火,然后就慢慢地降落在体育馆后的树林里。
这幅图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青春就是可以用来燃烧的东西,尽管匪夷所思吧,但是仍然可供燃烧。

↑ 以上这幅图片仍然是在墨尔本。似乎每个地方都有一座塔,只是东京和巴黎那两座借着游客比较多的缘故,知名一些罢了。北京大钟寺对面的试验田里也有一座这样的电波塔。从前放学回家的时候每每经过,我都会安慰自己,看不见东京塔,看看大钟寺这座也凑合了吧。
这幅图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塔是人类对天空的崇敬和对地面的厌恶。如果现实没重力的话,塔会倒过来,根植于天空。

↑ 以上这幅图片是08年秋天在意大利米兰。狭窄的街道上怪石横生,专为我这种边走路边玩PSP、从来不看前路的人设计——摔你个鼻青脸肿,肝脑涂地。这种在我看来是脑子进水、叵测用心的邪恶设计,在城市规划者眼中却成了时尚之都的代言词。
这张图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骑着小绵羊机车戴着头盔的真不一定都是尿糖偏高的卷发武士。

↑ 以上这张照片是09年春天在日本大阪,那里有关西最大的步行商店街。其中的百元店是穷人的天堂。百元店里面很多在日本打工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见到我说英文以为我是韩国人,而我说英文的唯一原因是我认为他们是日本人。后来我对他们说都这么晚了你们还出来打工真是不容易。他们说你都在飞机上打了十个小时的工了还要倒时差出来逛街,你才是真不容易。
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年轻人真不容易,天上地下满世界地给人家打工。

↑ 以上这张照片是2009年夏天在伦敦圣·詹姆士公园,描绘的是一棵紫藤树下人(我)畜(呆雁们)和睦共存的平静场景。紫藤树虽然花开狂野、枝干分明,但却在同时衬托出在其荫蔽之下乘凉的小动物们的内心之平和圆润。
这幅照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星球本身即为福祉,它的初衷是像蒂法一样守护你,像克劳德一样治愈你。如果有天它变身杰尼西斯(一个残次品)或者萨菲罗斯(他善用狱门),动不动就用台风海啸、疾病肆虐之类的大招来惩罚你,请在找出形形色色的借口来解释这些现象之前,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缺RP的事情,惹你居住的这颗星球生了气。
总之无论如何,都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你也曾是紫藤树下乘凉的小动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