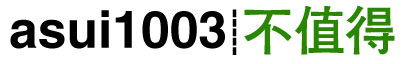杨敬如刚回到他工作的物流公司,马上感觉到气氛和平常有点不同。吃午饭的时候,他从工友嘴里打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守业,他们的一个同事,遭遇了车祸。他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然后被卷进后面开来的小货车轮下了——在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这种事并不罕见——现在人已躺到了医院里。这已经是前天发生的事情,碰巧杨敬如轮休了两天,等到他来向别人打听情况时,别人已快把这件事的细枝末节都聊遍了。
他最关心的是李守业的伤势。根据并不确凿的信息——因为没有人到医院探望过他——他的运气非常好,尽管当时旁观者都估计他肯定活不下来,但他却仅是受了点伤——当然是重伤——可是没有生命危险。接下来最头疼的是医药费问题。按道理这笔钱当然得那个小货车司机付,李守业自己连病都看不起,更别说住院了。可是,同样是根据道听途说的讲法,当时李守业把自行车骑到了只允许机动车通行的高架桥上——大概是为了赶时间或别的什么原因——所以事故发生后,交警认为主要责任不在小货车司机上。这就很可能导致,李守业要自己掏一笔医疗费,而他是无论如何掏不出的。但是,就杨敬如所见,在场并没有人对此表现出忧虑。“你知道吗,那个湖北佬终于不来上班啦。”他们面带欢容的如是说。或者,“别过分担心啊,医生也说他没事嘛。”这样安慰他。就仿佛发生意外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归根究底,部分原因在于李守业自己孤僻的性格。其次,假如他处在一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组成的团队里的话,情况会好一点。可实际情况是,除了他一个外省人以外,其他工友都来自广东省内各白话地区。或者来自潮汕语地区但早已学会了说白话的。这样一来,当大家聊天的时候,哪怕李守业就坐在旁边,也听不懂大家在说些什么。当然,也不会有人特地用普通话翻译给他听。假设有某个好心人这样做了,他得到的绝不会是大家的尊重,而是取笑。“哎哟,你的普通话好难听呀,拜托你说不准就别勉强啦。”大家会这样对待这个热心的好家伙。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子表现得与众不同,然后接受同伴的取笑。所以,除了工作上必须的交流以外,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和李守业说话。
杨敬如还听过这样一些传闻,事情发生在他应聘来这家公司以前,李守业曾经在领导跟前举报自己的工友上班时偷懒。尽管那个工友事后没有受到处分,但大家都因此开始排斥李守业。一个喜欢在上级面前打小报告的人,无论在哪个团队里都不会受欢迎。
那些外省佬永远都学不会遵守城市里的规则。”阿里对杨敬如说。他们一同坐在货车的尾厢,正去往送货的路上。关于李守业的事情,阿里已滔滔不绝地说了足有半个小时。“高架桥他也敢骑上去,他以为自己有几条命啊?”他又说道。杨敬如没有开口应话,但每当阿里说完一句,他的脸颊肌肉都抽动一下,挤出一个“冷笑一声”的表情来,仿佛既认同阿里的观点,同时又对此不屑一提。每当他认为别人在胡说八道,但又不敢反驳时,他就摆出这副表情掩饰。车厢因为凹凸不平的路况而摇来晃去,他的身体也随着摆来摆去。阿里那颗硕大的脑袋也因此离他忽远忽近。他们坐着的车厢其实并不宽阔,而且还堆满了装着货物的纸皮箱。两个人在正对着的位置上斜身错开而坐,以避免在近距离你眼瞪我眼的尴尬局面。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和李守业共事,而公司里很多送货业务偏偏又需要两个人合作完成,所以,还算是新来的杨敬如有了不少和他一起外出干活的机会。两人也是坐在这样狭窄的车厢里,但话匣子却总是由杨敬如打开。“你为什么跑来广州打工?”“你的亲人在老家都做些什么?”“种地吗,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种地?”他喜欢提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出乎意料的是,李守业并不像旁人说的那么难相处。他确实很少主动开口说话,而说起话来也确实是一口难懂的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但只要杨敬如提了问,总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答案。他的话里从来没有那些让人讨厌的措辞技巧,他从不避重就轻。比如你问他对某个公司领导的看法时,“我不喜欢他。”他会这样回答,直白明了,有时还配上憨厚的一笑。而假如拿同样的问题去问阿里,估计他会这样回答,“我和你一样讨厌他。但是你也明白,一家大公司的管理人有时就得这样办事,你说对不对?”他会反过来逼你表态,以提防你日后在领导面前拿着这些只言片语搬弄是非。
除了性格率真以外,李守业还有一个显著的与别不同之处,就是他干起活来从不嫌脏怕累,也从不偷懒。只要是属于他的份内事,你完全不需要督促提醒,他自己就会办得妥妥贴贴。同时,他还遵奉着一些很原始以至于可笑的道德方式,以达到不占别人便宜的目的。比如说,杨敬如抽烟的时候一般也递给他一根。那么下一回,无论是谁想要抽烟,或许又是杨敬如,当他再掏出烟来时,李守业会一把按住他的手,一脸严肃地说,“轮到我了。”然后掏出自己的烟来递给他一根。
“轮到我了。”——当第一次被李守业这样拦住的时候,杨敬如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哪里冒犯了对方。事后回想起来,他不禁哑然失笑。乡下人真有意思,他心里想。
“这是他自讨苦吃,根本不值得同情。”阿里继续说道,“那些北方佬,个个以为广东遍地是黄金,一窝蜂似地蜂拥而来,结果呢?全部找不到工作!变成一天到晚游荡在火车站周围,却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你说说,他们除了干犯法的事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和李守业没有关系啊,他不是找到工作了吗?”杨敬如忍不住说。
“你说什么?”阿里凶巴巴地反问道,“我没有说他,我在说那些北方佬!”
路颠簸得很厉害,车厢里一些没固定的杂物不断撞击着车壁,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后厢门关得仅留一条缝,外面的光线艰难地从缝隙里渗进来,即使加上前面连通驾驶室的一小面透光窗,车厢里也暗得要命。
“你觉得正常人会把自行车骑上高架桥吗?”阿里忽然问道。
“什么?”杨敬如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如果人人都把自行车骑上高架桥,结果会变成什么样?”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全垮掉,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全部垮掉!他们根本不知道要遵守规矩,把这里当成自己老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不仅仅是交通规则,交通规则还只是个小问题而已,和他们在治安方面搞出来的破坏相比,交通问题简直不算是个问题。”阿里气鼓鼓地说。
杨敬如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打量着阿里,从他蓬乱的头发,麻石般粗糙的脸部肌肉,还有外弓着的臂肘下按在双膝上的两手,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外貌和动作特征,来判断着他忽然冒出的气愤是不是因为自己刚才为李守业的事顶撞了他一句。不值得为这事惹火他,杨敬如心想。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一包压得扁瘪瘪的红双喜,在手掌上敲了两下。两根烟滑了出来,他把其中一根递到阿里嘴边,阿里咕哝着谢了一句,作势抬了一下手,但没接烟,却直接用口叼住了。杨敬如又拿出火机,在摇晃着的车厢中艰难地为阿里点着了烟。阿里狠劲地吸了一口,然后呲起牙把烟云从嘴唇两边呼出,而烟嘴仍咬在中间门牙部位。
杨敬如接着给自己也点上了烟。没过多久,车停了下来,车厢门被哐地打开,暴烈的阳光蓦然打在措手不及的两人身上。杨敬如眯着眼站起来,阿里已跃到了地面。一个套在一身黑色西装和领带里的客户,从前面驾驶室里跑了下来,一边挥舞着握在他手里的一本卷起来的32开软皮抄,一边对着两人喊道:“货物要搬上五楼,你们跟我来吧,不过,得辛苦你们跑快两步,因为我很赶时间。”
杨敬如把一个装着货物的纸皮箱子推到车厢门边,阿里已经站在下面,把他那宽阔的背脊对着他,身子微侧,手向后伸着,像米隆的那尊著名雕像。杨敬如把箱子扶到他背上,他双手马上扣紧,腰往前猛一弓,箱子就此转移到了他的背上。东西到了身上后,他一刻都不耽搁,马上往前奔去。旁边的黑西装见状则几个箭步冲到前面带路。
杨敬如把另外一个箱子挪到门边,然后跳下车,贴着车边艰难地把箱子蹭到自己背上,然后一边低声诅咒着一边朝前面两人追去。当他气喘吁吁地赶上阿里时,他正和黑西装为一件小事情发生争执。
“这里每星期六日货梯都不开,我们走那边的楼梯吧。”黑西装说。
“货梯不开,但客梯不是开着吗?”阿里反问。
“客梯不能用来运货。”
“谁说不能?”
“物业管理看到会骂的。”
“让他骂好了,反正是骂我,跟你没关系!”说完阿里也不管他,直接按亮了客梯的小三角按钮。等杨敬如和阿里都把箱子卸到电梯里后,黑西装才无可奈何地跟着闪了进来。接下来,两人又把箱子搬进了黑西装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那里面就像刚经历了一场地震,乱七八糟的杂物堆满了一屋,必须得先清理清理这些东西,才能腾出地方放下楼下的那一整车厢货。
黑西装看到这番情景,表现得似乎比杨敬如和阿里还要惊讶,“哎呀,我早就吩咐他们先把这里收拾好,他们一定没听到!”他大声对自己说道。当然,旁边的两人肯定也听到了。
“这里要收拾一下。”阿里小声说。黑西装连忙应道,“对对,这里肯定要收拾一下。要不这样吧,你们留一个人在这里帮忙挪挪东西,另一个人去搬货吧。”
“我收拾吧。”阿里一边说一边已动起了手来。他先把一张带轮的电脑椅推到墙角,回头一看,杨敬如还愣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快去啊,你不想下班了?”他没好气地催促道。
杨敬如一个人下了楼,跟货车司机埋怨了几句楼上的情况,然后又艰难地扛起一箱货上楼。可这一次,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保安,任凭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许他进客梯。
不值得跟他一般见识,杨敬如对自己说。最后,当他把全部约四十箱货都搬上五楼后,已累得双臂抽筋。而阿里负责的工作,只是把屋子里的东西草草拾掇了一遍,然后把杨敬如搬来的箱子按一定的条理堆整齐。当所有事情都忙完,他从杨敬如发抖的手里接过香烟的时候,他甚至连刚上楼时出的一身汗都晾干了。
在回去的车上发生的一切,和来时的那幕仿佛是同一部电影里的上下半场。阿里仍在絮絮叨叨关于李守业的种种是非,而杨敬如装出一副累得连话都说不出的样子,一言不发。“你是后来才来公司的,以前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在李守业来之前,我们都没那么累。他才一来,就搏出位,讨好领导,抢着干活,本来两个人干的活,他一个就扛下来。后来弄得领导还以为我们其他人都在偷懒呢!你说说,他这不是害群之马吗?”
杨敬如懒得搭理他,货都卸空后,车厢里空荡荡的,他也顾不得脏,直接躺在地板上。
“你觉得累吗?”阿里问。
“嗯,挺累的,我刚才一个人搬了四十箱货上五楼啊。”
“所以说啊,假如换在以前,这样分量的活应该派三个人来的。但自从李守业搞坏了我们的规矩后,公司只派两人了,当然累啊!”
杨敬如侧过头,颇费工夫地分辨阿里到底是在耍自己,还是把这些话当真了。停顿了有那么十来秒,他才试探着问,“所以这都怪他喽?”
“当然啊!”阿里斩钉截铁地道,“肯定的,这都是他闹的。”
“我们那么累,全都该怪他?”
“是啊,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明白了。”杨敬如说。不值得跟他争这个,他心里想。
“像我们这些做苦力的,就是社会上被剥削得最多的。我们干活最累,报酬最低,什么福利保险都没有。而且老板什么时候想炒掉我们,连一分钱都不用赔。这个社会哪里有公平?一点公平都没有。有钱有势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就不用管法律。我们就算再怎么命苦,也不能吃那么多亏呀。我们辛辛苦苦出一趟车,才拿百分之二十的钱,老板什么力气都不用出,却拿百分之八十——哪里有公平?”
“对啊对啊,一点都不公平,社会太不公平了。”杨敬如随口应道。
“就是呀,所以才来气嘛!我们本来团结一致,还可以跟老板提提条件。但李守业这种人跑出来完全是在捣乱,专门讨好老板,变相使我们被剥削得更深。只要一天有李守业这种没骨气的奴才,那些老板就一天不用慌。我们什么权利都不会争取到。因为只要我们不干,老板就去找李守业那类人干,所以我们根本没法反抗,只能眼巴巴被剥削。而这,全部都怪他!”
“我听说,李守业曾经在老板面前告过别人的状,说别人偷懒,是真的吗?”杨敬如忽然问道。
“一点都不奇怪,他就是这种人!”
“不,我不是问奇不奇怪,我是问他有做过这件事吗?”
“他有没有做过都一样,他就是这种奴才!我当然觉得他很可能做过,但我没亲眼看到。”阿里愤愤不平地说道。
杨敬如接下来没有再说话。他记得,当初听别人提到李守业出卖工友的事的时候,发言的那人说这件事是从阿里口中听来的。但现在阿里也说了,这件事他根本没有亲眼看到,他只是觉得李守业是这种人而已。不过,杨敬如不打算追问这件事情。就像他爸爸传给他的那句口头禅所寓意的——这种事不值得深究。
一个小时后,杨敬如和阿里已经坐到了公司对面的兴旺餐厅里,同桌的还有阿亮、小程和李明。这时候天还没有黑,但这五人都提前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定额。他们公司每天管员工一顿饭,而这宗生意就由兴旺餐厅来承接。他们凭着公司发的餐券,每天晚上来兴旺餐厅领一份两荤两素的快餐,和一碗足以与清水比清澈的冬瓜汤——每天,永远都是冬瓜汤。
阿里他们在餐桌上的话题,翻来覆去不外乎就是“社会不公平,生活很艰难,有钱人很糜烂,当官的很腐败”之类的,几年来没有换过,估计未来几年也不会换。杨敬如在这些谈话里永远不是主角,但却是最好的听众和信徒。每当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他也跟着笑得饭都喷出来,使人认为他和发言者早就有着某些类似心有灵犀式的共鸣。故此,尽管他几乎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话题,但所有的发言者都觉得他是一个最坚定的同盟者、共路人。有时候他甚至会凭着出色的表达能力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在别人怀着明显的想法却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一言万钧地加以点拨,并随之迎接大家轰然如雷鸣般的笑声和叫好声。先后有好几个工友在餐桌上夸奖过他“说话最到位”。
然而今天,这位平常“说话最到位”的乖小伙,却在餐桌上感觉特别的别扭。这是因为阿里把白天关于李守业的话题又延伸到餐桌上来了。所不同的是,在光亮的餐厅环境里,在四名工友的目光环视下,当大家哈哈大笑或愤愤不平的时候,他也只能跟着哈哈大笑或愤愤不平。他甚至不能不表态。因为在这种大伙聊得兴高采烈,尤其有的人还喝了几杯啤酒的情况下,谁要是不跟着表示赞同那跟提出了反对意见没什么两样。而在他的社交哲学里,跟别人处好关系的秘诀就在于始终跟别人保持观点立场的一致——就算心里不一致,表面也要一致。
这一幕闹剧的高潮是这样到来的:当杨敬如喝了几口啤酒,继而不够谨慎地在席间向旁人打听起李守业住院的医院后,大家以近乎高呼和狂喊的声调质问他是不是准备去“探望那个叛徒”。开始的时候,杨敬如几乎想要承认了。老天爷啊,堂堂的一个男子汉,难道连去探望自己受了重伤的工友,都要遮遮掩掩吗?可是,长年养成的警惕心在最后关头拉了他一把。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假如在这个场合承认了这件事,那么无论他的态度是多么谦卑,措辞是多么谨慎,最后,大概在两天之内,公司里所有的工友都会听到一则与事实不尽相符的夸大传闻,内容是关于他杨敬如如何傲慢地拒绝与大家为伍,而执意为李守业出头。当然,凭藉他一直以来的任劳任怨和谦卑恭顺,大家倒未必因此就孤立了他。但也绝不会像现在这般推心置腹了。这些都是要好好掂量的,到底值不值得。而很明显,杨敬如对自己说,为了这个不值得。
“去探望他?”杨敬如说,“你们没开玩笑吧!”借着一点酒意,他成功地掩饰了自己此时异样的满面通红。“假如不是因为他,我今天会累成这副样子吗?你们看——”他抬起双手,臂腕向外,只见一道道因皮下出血而泛起的粉红色划痕触目惊心地盘踞在他两臂上,这都是刚才那四十个箱子留给他的纪念。“都是他害的,我跟他有血海深仇!”他扯高嗓子嚷道。阿里几人完全被他逗乐了,两三支胳膊同时挂到了他的肩膀上,鼓励他,大家重复着“血海深仇”四个字,大声喝彩,仿佛天地会的同志听到新成员喊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一般,差点要把他举起来抛到空中庆祝。
稍晚一点,当夜幕完全降下来之后,杨敬如一个人赶到了工人医院。他和阿里几人分别后独自打电话给公司经理,问到了李守业被送来了这里。他跑进医院大厅,这里人并不多,因为是晚上,咨询台后面没有站着值班护士。他往后面的住院部跑去,绕了几圈后终于找到了护士值班室。他以为应该向护士报上李守业的名字,然后等待护士在一本厚厚的住院病人登记簿上找出李守业所住的病房,就像电视剧里常演的那样。可是,护士根本不想知道病人的名字,更没有查什么资料。她问他,病人什么时候被送来的,以及得了什么病。他按照经理告诉的情况回答,李守业是前天下午被送来的,因为车祸,双腿骨折。
“前面拐左,直走到大厅。”护士说。
“什么?”杨敬如愣了,“不是在病房里吗?”护士抬起头,直直瞪着他看了三四秒钟,因为戴着口罩,分辨不出她此时是什么表情。“前面拐左,直走到大厅。”护士又把话重复了一遍,语调里不挟带一丝感情,就像说话的是一台复读机。
杨敬如迟迟疑疑地朝护士指示的方向走去。假如她弄错了的话,我一定不放过她,他心想。在踱过长廊时,他发现连走廊两旁都错落地安置着几个临时床位。当他走进尽头的大厅里后,只见七八张带轮的临时病床分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每一张病床上都躺着人,有的床边还守着病人的家属。这时大约是晚上九点,不算晚,屋里装了十几支光管,但有半数大概为了省电而没亮着,其余的里面还有一两支忽明忽暗地闪着,估计快要报废了。这个大厅没有窗,只有两扇门,但其中一扇牢牢地关着,大概早已被封闭。而杨敬如就是从另一扇门走进来的。
他从左边走起,沿着墙壁绕了一圈,房间约有五六十平米,一下就走完了。李守业并不在这些床位上。杨敬如有点生气了,那个态度冷峭的护士,也太不敬业了。他往房间外走去,想好好地责难她一顿,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在大门斜对面的走廊,一张漆成灰色的临时病床上,李守业正正地仰躺在上面。刚才他走过来的时候,因为一心以为李守业在大厅里,故此疏忽了观察左右的病床。
从侧后方看去,李守业身上穿着蓝白竖条的住院服,脑壳上缠着白纱布,肚皮上盖着一块白色的棉纺布,就像盖在死人身上的那种。他的双手无力地搁在腹部的白布上,苍白得浑如一体。他的双腿,打了厚厚的石膏,脚踝位置被固定在从床上方铁支架上呆下来的绷带上,略微离开床身。他刚才并没有看到杨敬如从他身边走过,但他也没有闭着眼。他正茫然地望向病床上方,仿佛那上面不是苍白昏暗的天花板,而是广袤的星空。
这整整的一天,杨敬如都心神不宁,心急火燎地盼着这一刻,盼着见到李守业,可真来到了这最后一段路,他却感觉每迈出一步都要花去千斤的力气。他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应该站到李守业的床边,先向他道歉,因为从他被送进医院到自己来探望他已足足隔了两天。然后他要鼓励他快点好起来,并告诉他自己有多么重视他。因为当初自己刚到公司上班时,只有他没把他当作一个小红领巾看待。此外,无数次当他被沉重的货物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时候,又是他无私地分担了他的份内活。而他向躺在病床上的他倾吐这番心声的画面,白天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反复上演了无数遍。终于,这一幅画面要穿越到现实中来了。他艰难地挪到了李守业的床边,发现自己全身都已僵硬。本来以为轻而易举的事,却有着超出想象的沉重。他才刚张开嘴,片刻前餐桌上的情景忽然就在他眼前闪现,他惊惶失措,空洞的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咽了口唾液,再次尝试把要说的话吐出来。这次他终于成功了,可是同时他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得跟陌生人的一样。
【论坛讨论】
陈鱼:
1.他正茫然地望向病床上方,那表情就和杨敬如虔诚地怀了一辈子革命理想的父亲听闻单位的老厂长因为贪污而被抓了之后流露出来的一样——失落,迷茫,难以置信,但不愤怒。这是一个很无厘头的感情爆发点
也是个很不到位的长句子 不好
2.“你救过我一命。”——这个东西放在结尾
太重了 也刻意 前面完全没有提及 杨和李的旧事也是点滴积累 结尾突然来了救命之恩 就显得很假很虚了 而且 把原本牢固、细致、微妙的人物关系打破了
——杨敬如的一意孤行和泪如雨下都成为一个知恩图报的旧套路——我甚至以为,在看到“他刚才并没有看到杨敬如从他身边走过,但他也没有闭着眼。”的时候
作者会让杨敬如最后折返回去 没想到还是看成了
3.asui1003
的题目始终不是很好
asui1003:
谢谢陈鱼老师,老厂长那句确实突兀,我对你的看法很认同,我会在二稿时删去的。
而最后故事的结尾,其实是我最初构思这个故事的重心,在写之前,心里的打算就是写一个“救命恩人在被人污蔑却不敢为他出头的窝囊汉”。但当我真正动笔写的时候,完全就脱离了这个故事核。最后我把结尾写上去,自己也有怀疑。我自己无法分辨这个故事是不是已经不能配这个结尾了,但我没有预作铺垫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我构思中就是想直到最后才让读者知道原来两人间有这样的恩义在。我并不想过早让读者知道原来杨敬如是个这么窝囊的人。但我在读到你的意见后,我完全赞同你的叙事美学,我也认为如果从头把这篇小说读下来,结尾是用你说的那种方式会更具感染力,也更真实质朴。我上一篇《一件小礼物》其实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我在动笔前先有一帧画面,然后我的写作本是为了把这帧画面带出来,可是我写作时缺少整体感,写着写着就心随笔走了,就追逐着细节前进了,直到最后才发现已经偏离了预想的那帧画面。这时我就有两个选择:要不就舍弃小说最初的立意,创造一帧新的画面;要不就将错就错看看把原来设想的画面安上去会怎么样。现在我读到你意见,我知道我选错了。可是,回想起来,在我写到最后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想不出以你提议的那种方式结尾的,因为我当时急躁了,我发现原来预想的结尾安不上去,我光顾着从技术角度想法子勉强安上去,而不是继续追随已写出来的90%篇幅的故事的脉络,而让它自然发展下去。这个教训真的很宝贵。非常感谢你,以及每一次在我帖子后面回复的各位的金玉良言!
陈鱼:
1.叫陈鱼就行啦
2.但我没有预作铺垫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我构思中就是想直到最后才让读者知道原来两人间有这样的恩义在——嗯
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 这个技术可以做 但是 不应该是——借用一个熟词“包袱” 这个包袱不该是“救命之恩”这么大的东西 它和前面的细微末节的气息都不相容
随便举个例子 最后是 你曾经在下雨天我自行车掉链子时借我自行车而自己却淋着雨走回家 也比 救命之恩好一些 最后的东西 太大了 完全把前面真实的气息打碎了
从一段生活突然变成了一个肥皂剧
asui1003:
陈鱼你好,我原本设想的“救命之恩”确实太重了,我经过一天的认真考虑,也觉得破坏整体感。我刚才已用修改稿覆盖上去了。因为怕在这之后才读到正文和你上面的回复的朋友因不清楚缘由而发生误会,我特别注明:正文已经被我编辑过,陈鱼在写意见时读到的初稿已被覆盖。二稿的修改全部在小说结尾的10%篇幅里,前面90%的内容没有变更过。
最后,再次再次感谢陈鱼诚恳并且颇具专业素养的阅后意见,我渴望交流和进步,我也会多参与到大家的讨论中去的!
乌鸦十三:
这也是卡夫卡系的,很亲切。
没有看过上一版,就这一版的结尾来说,已经不错了。
“这次他终于成功了,可是同时他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得跟陌生人的一样。”
没有出现具体的那句话,因为不需要出现。不出现之中蕴含的可能性所带来的丰富感觉远远超过你所能写出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你只能写出具体的某一句话,现在却是无穷的。无穷尽的可能。
另外,感觉题目即使叫“陌生人”也会比现在的好。“不值得”,这个已经对不上了。
asui1003:
谢谢乌鸦十三的观点!原本的结尾是最后透露出李守业曾救过杨敬业的命,写前构想的时候感觉挺好的,前面一直是杨窝囊地忍受着大家对李的污蔑奚落,不敢反驳,最后才带出原来李还是杨的救命恩人,这样制造一种情节上的震撼效果。但实际上写出来后发觉效果并不好,其实在没贴上来之前,甚至在我没写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已经很忧虑这个问题了。贴出来后最心虚但又最心急火燎想听到的,就是大家对结尾那样安排的评价。当陈鱼的回复说道“宁愿他们在医院错过了也比抛出那么重的一个包袱好”时,说不出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观点更接近我的叙事美学。但在写的时候,因为我脑海中先存有这篇小说的纲领,我就是为了描绘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窝囊的男人眼睁睁看着恩人被污蔑却不敢反抗,反倒被胁迫着顺从了强势一方,直到最后在恩人的病床前痛哭流涕忏悔——才动笔写这篇小说的。然而不只一次了,我发觉我驾驭不了一次有预谋的写作,而只能在故事前进的过程中被动地跟跑。我现在也不知道应怎样锻炼这方面的能力,难道说要在动笔前把每一大段落的提纲都先写出来?
黑天才:
改过之后好得多,以至于最初的时候看不太懂你们俩在说什么。看得太晚就是不好,能这样瞬即修改自己小说不足的情况还是很少的。一方面大部分人都对自己更有把握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你开始真的警惕“包袱”这个东西的局限性。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小说的前三段告诉别人的。有点马后炮了。
这个小说几个部分都很好,但也还应该更压抑一点,或者说,对这些人物,更不客气一点,但也不是一定要到了角色扮演的过分,而是在语句遣词上的。要给自己提一点阅读要求,要确定阅读时达到如何的一种效果。
asui1003:
谢谢黑天才的意见,遣辞用句方面,我还很稚嫩,写作经验不多,我相信我多写了会越来越好的。现在哪怕我希望在文体上有突破,也是力有未逮的。
此外,关于结局被我修改了一次的事,是这样的,首先我的自我怀疑感是很强的,其次文学创作方面我也确实没太多心得,并非过分谦虚,而是确实应该多听别人的意见。三是那个结局本来我就很不自信,隐隐觉得不妥的,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加在一起,导致我一读了陈鱼的意见,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陈鱼在别人的作品后面给的意见,我也读了一些,往往都切中重点,言简意赅,而且恰巧都是我的水平能够理解的。这点真的很好。还有就是,我这篇小说原来的构思就有问题,如果情节的结尾有那么大个包袱,是不太适合我的叙述风格和题材倾向的。我从构思最初就走偏了,而不是在写作过程中才出问题的。我在下一篇写作中会汲取这个教训。
小5:
我觉得这篇小说很不错,就是包袱的问题我和前几位的观点大致相同,对于主人公应该更加“激烈”一些,达到好的效果,另外在文字运用上总感觉有一点点捉襟见肘,希望再老道一些,呵呵,仅供参考。感谢你评论我的小说,今后多交流!
黑天才:
你对小说的把握和理解还是挺好的,而且写作上的进步也比较快,能用不太多的几个小说,找到该找的点。所以请接着写。
乌鸦十三|困难的困难
问题一开始就很清楚:写一篇评论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里,我不但要紧紧抓住小说本身,还必须对我本人并不熟悉的种类繁多的体系,手法和风格做出判断并将这种判断用尽可能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
这真的很困难。大部分时候超过写小说时的困难,特别是当你很认真的想对某篇你有想法的小说做出评论的时候。
关于《不值得》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题目。但这与创作手法有关,作者首先有了与这个词有关的画面才创作出这篇小说——虽然小说脱离了他的控制,实际上,走向了比他的设想更好的方向——这个时候,该怎么修改这个题目呢?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它,但是没办法,这是个大困难,因为我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第二个困难是,当我读完全文时——我还没有读完全文时,我觉得前面的部分还是不错的,用词遣句上有卡夫卡的色彩,但是融入了个人风格——结尾部分的出色让前面所有的铺陈都显得落后及不合时宜。当我重新再读完一遍时,我确信,从“稍晚一点,当夜幕完全降下来之后……”这里开始的结尾部分远远超出了前面的全部。它那么的含蓄,又有控制力,简单而清晰,情绪慢慢浮起,在最后的几句话到达它的高潮:
“……再次尝试……同时他也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的像陌生人一样。”
像是一个重音转低音,又戛然而止。
这确实是给作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画面,所以也给读者以最深刻的印象。可前面怎么办呢?一部小说怎么能只有结尾?没有前面的弱的部分怎么来到达这个强的结尾?这更难了,更困难的困难,更没有答案的问题。
最后的困难,我是不是在对我不确信的东西做出自以为是的判断。asui1003的所有小说都有着我所不能及的现实因素和非常顽强的想对小说做严谨控制的努力,他试图完全掌握小说的情节,感情和逻辑走向,这没有错误,尽管这和我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背道而驰——我早就放弃制定提纲和控制结局,并且狂热的相信无论怎样混乱的情节都能在小说自身完整的体系里自圆其说——但绝对不是错误的。可能他只需要时间,去找出准确的方法,在控制里释放自己的想象,让他观察到并且非常确定的现实可以承载更多的其他现实,甚至他本人想象不到的现实。这我根本不能确定,更不可能做出论断。
所以都是困难,困难的困难,困难的困难的困难。
不过,超越了这一切的一件事情是,他和我都还能写下去。
好像写下去反而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我甚至还这么相信,asui1003以目前的写作速度再这么写两年,就将不存在任何困难。
所以写下去就好了。这是最简单的。我也很乐意为他更多更好的小说写出我的想法,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写出来,写出来,只管写出来。
不管有再多困难,困难的困难,只管写出来。
这是最简单的,最真的。
只管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