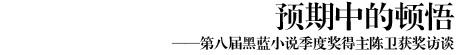|
|
提问:赵松
访谈时间:2005年10月18日
赵松:离我们上次那个访谈,有多久了?
陈卫:两三年了吧,有吧?
赵松:两年。
陈卫:哦,感觉很久了。
赵松:是啊。
陈卫:那个访谈我后来看了一点,觉得太严肃了。可能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做访谈,有点严肃。
赵松:嗯,那时确实比较严肃。
陈卫:虽然节奏什么还是比较放松,但骨子里还是有点紧的。
赵松:这两年实际上我们的交流不如那时多了,远远不如。
陈卫:现实交流少,神交多嘛。
赵松:不过这种交流的减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多事实际上彼此已是心照不宣。
陈卫:做,肯定比老交流重要。
赵松:是,过度交流有时候也是非常的反应。
陈卫:蜜蜂肯定不是老开会。
赵松:嗯,尽管它们成群结队。
陈卫:他们在花朵上忙得抖抖的,哈哈。
赵松:呵呵,我昨天在网刊有前言里也多少提到了这种感觉。就是说,交流减少后,看你的文字反而更自然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文字来面对你这个人。
陈卫:其实我并不知道我的东西在你和其他朋友眼里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你。
赵松:实际上我对你的文字始终都有种担忧,以前我也曾提起过一些,就是偏紧。因为你对文字的要求非常严,近乎苛刻。
陈卫:其实呢,我自己太清楚自己这个了,近年来这在我心里已经不是问题。
赵松:嗯,我觉得从《那时我们这样杀死老师》到最近的这几个,这种担心基本已经被化解掉了。
陈卫:而且我更觉得: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紧不起来。从松到紧比从紧到松要难多了。
赵松:是,肯定要难得多的,从松到紧是上坡。
陈卫:当然,最好是能做到松紧有度。所以一开始紧一点没事。但不能老紧。要懂得松的意义。
赵松:当然我说的紧跟你说的可能还不大一样。
陈卫:我觉得基本上一样。因为我能理解你说的紧。我心里理解的紧也是那样。
赵松:其实说的是语言的一种状态,语言存在的状态。
陈卫:是啊,我知道,紧,就硬嘛。
赵松:是。
陈卫:密度过高。
赵松:会影响气息在流动,会影响空间感的确立。
陈卫:这一点到现在仍旧不是毛病。但要清楚它的问题所在。
赵松:还不能说是毛病,因为毛病太具体。而我们说的紧与松,实际上并不是很具体的东西。
陈卫:实际上也有把紧弄得很好的。我觉得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画像》就很紧,那也没成问题,我觉得那也很好。
赵松:乔伊斯的那个,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么,他要结构上非常精到,想的很多。压缩得很密,但总体上控制的相当好了已经。
陈卫:是的。
赵松:结构的语言状态,这样说可能更进一步。就是说,紧,不应表现在表面上而是结构上。坚实的河床,流动的河水。
陈卫:恩,是的。这些我还在学。当然,目前对我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过程中学习改变。
赵松:当然。我记得我看完你的最近的两个短篇以后,感觉很高兴。
陈卫:最近贴论坛的这两个,本质的目的就一个:就是想:我来松一下呢。
赵松:尽管你说了它们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基本上写完了就发了上来,但我觉得它们恰恰可以证明你目前的写作状态到了什么地步。
陈卫:《宽躺椅》,我还是有点喜欢的,不过它们是让我休息的。
赵松:那只是你的想法,它们有它们自己的状态,而且呈现出来了。
陈卫:我想在做一个大工作前休息一下,重新尝一尝“哗”一下的感觉,我本来想一天一篇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用了电脑之后反而更耗体力还是怎么的,一天只能写那么多字,写多了,体力跟不上了。也不是那种纯粹的跟不上。就是感到适可而止了。写完《宽躺椅》正好被去北京掐断,但也无所谓了。还可以再来嘛。
赵松:两个漂亮的小练习曲。这个词我昨天也用在对马牛的评价上了,小练习曲。很多好的古典音乐家都有过很多漂亮的小练习曲。因为这种东西常常会触发很多重要的因素发展出来。包括技术层面的东西。
陈卫:没错。休息嘛,一休息就有歪念了。所谓酒足饭饱思邪念嘛。
赵松:实际上看你的《爸爸像西瓜一样》和《那时我们这样杀死老师》的时候,有阅读的愉快,但惊讶并不多。只是觉得你在温习一些东西,恢复状态,同时更新状态。
陈卫:《爸爸像西瓜一样》和《杀死老师》是不一样的。《爸爸》的恢复性太明确了。杀死老师已经恢复过来了。
赵松:但那两个的文字感觉弹性与韧性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爸爸》当然还在恢复,老师是完成恢复,而且很明显,没有《老师》,就没有后面的《定淮门》和《宽躺椅》。
陈卫:《爸爸》,是在我准备往一个方向走时要作调整时所必需的恢复,所以有种累在里面。
赵松:是,挺重的感觉,文字本身的,字里行间的。
陈卫:正因为在恢复,甚至有点强行恢复的感觉,所以不累不重不行。必须绑沙袋。《杀死老师》也累,但累得有方向了,是我需要的劳累,劳累得舒服。《定淮门》和《宽躺椅》就是休息。《宽躺椅》嘛。
赵松:前者像整理旧房间,毕竟不能全更新,所以会累,因为故有的还多。
陈卫:没错。《杀死老师》造了房子。
赵松:后面的《老师》已是新房间了,也累,但是心情好,因为随后新的东西都会随之而来。
陈卫:但《杀死老师》之后真正的新东西并不是《定淮门》和《宽躺椅》,应该是这两个之后的。
赵松:嗯,那当然,小插曲,是个预兆。
陈卫:总之,我觉得现在一切才真正开始。非常清楚了。并不是清楚具体的。而是,我清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了,大的方向清楚了,或者说,大的节奏也清楚了。
赵松:实际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你似乎进入了一种半隐居的状态。
陈卫:其实我一直这样。我一直需要的就是这样。热闹时都是假象,或者被迫,除非是非常开心,突然想释放一下。前面黑蓝刚刚开始,我可能比较忙些。
赵松:但这一次我感觉你基本上保持一种距离感,无论是与论坛,还是与朋友。
陈卫:我其实更适合这样。这样我的呼吸比较通畅。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关注朋友或论坛。
赵松:以前看你的文字,两年前的,感觉你习惯于用强,像锋利的刀一样,一路地挺进,不知有退。
陈卫:用强都是被迫嘛。当强者较少的时候,我只能硬撑了,呵呵。
赵松:表现在文字里也是,我记得我说过你的文字有金属感。
陈卫:现在我更清楚艺术在里面,在底下,在中间。
赵松:嗯,所谓百炼钢化成绕指柔吧,我觉得你这两年做的事就是一个“化”字。
陈卫:既然人类没什么好积累的,那过去已做得很好的我们确实没必要再去重复。这种进进出出的感觉必须保持。否则不是会窒息嘛。
赵松:但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安全感的需要,人们还是喜欢积累一下的。
陈卫:我们现在就是要放弃安全感。我是指在写作上。
赵松:这是个困难的选择。
陈卫:我们以前太需要安全感了。我这两天阅读下来更深地感到这一点,实际上,人,本来就没什么安全的。
赵松:因为很多时候对安全感的需要是近乎本能的。
陈卫:跑远了也不危险,没根了也没危险。
赵松:说到阅读,我倒是很感兴趣,特别想知道你在这两年的阅读是不是更多的倾向于古典的东西,比如说司汤达。
陈卫:司汤达,也没通读。读了两三本吧。主要是没去买书。陈侗他们做的午夜文丛也读。主要是古典的和午夜文丛。
赵松:我觉得这种阅读方向在你以前是比较少有的。
陈卫:其实我一直在读古典的,歌德和纪德都很古典,在某种意义上。
赵松:那以前的读与现在的读有什么差别呢。但我感觉似乎现在更能看到古典的影响,不是技术上的影响,而是气质上的容量上的影响。
陈卫:没什么差别,我一直没把他们当古典看。古典的和最新的,我感到都有营养。最新的,就是指午夜这一拨。但我并不希望午夜成为某种概念,我并不希望我说午夜或者说新小说,我越来越觉得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赵松:是,那只是个多方便些的称谓,什么都不代表,多少方便些。
陈卫:我只知道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的重要性至今没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新一代这些人,绝对不是人们概念中理解的那样。
赵松:需要前提,任何重视其实都是需要有前提的。对现在的发现与对过去的发现是同步的,不会单一存在。
陈卫:他们的努力细至毫发,对小说的重新思考非常有意义。
赵松:有点像科学家们,研究得极为深入,入到基因里了。
陈卫:但他们不是研究数据,他们研究感觉。
赵松:研究构成,研究生发,给感觉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得以成像。
陈卫:专门发掘已有的小说中忽略、却在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常值得重视的感觉。这很让人激动。
赵松:新小说家们提示了方法的可能。
陈卫:因为生活并没陈旧。不仅是感觉没陈旧,甚至材料也没陈旧……
赵松:材料无所谓新旧,生活也是一样。
陈卫:不,我的意思是:可以入小说的材料并不老是那些概念中的爱情啊、战争啊、社交啊什么的……
赵松:那当然了,那只能说是题材,而在真正的当代小说里,我觉得题材都是假像。
陈卫:我们可以谈一只杯盖子齿纹上的茶叶垢嘛。
赵松:我也可以只谈到茶叶。
陈卫:但是茶叶已经被文化了,已经被概念了,即便你再本体,你也容易落入象征、隐喻……
赵松:能把茶叶从概念化中解放出来也是一种角度,当然会很难。
陈卫:我的意思,怎么说呢,我们还有新材料可以发掘。当然,问题肯定不是为了新材料,对艺术而言,材料当然没有新旧,但我们必须知道“还有新材料可发掘”,而不老想着“永恒主题”“新鲜感受”什么的。
赵松:我觉得是生产方式的更新使新材料的发掘成为可能,哈哈,这种腔调很像科普讲座。
陈卫:是的,你这话没错。
赵松:比如说纳米材料。
陈卫:这个我不懂,
赵松:这个你可以查一下。
陈卫:我一直以为是一种泡沫。当然知道不是。
赵松:呵呵。结构方式发生改变,造成了材料的改变。
陈卫:恩。
赵松: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集成块……
陈卫:我物理化学只有初中水平。
赵松:当然,不然我怎么会动用我这高中的物理,
陈卫:这些得找我哥,摩托车配件啊,他是顾问,电路啊什么的……
赵松:嗯。最近一段时间你比较欣赏的作家,国外的,有哪些呢?
陈卫:我没看出那些古典的和这些新的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我是把他们放在一个精神系统里来看的。但在接受营养时肯定有不同。从司汤达身上学的和从加伊身上学的肯定不一样。
赵松:是,就像中药西药的差别一样。
陈卫:我刚刚看完《我的大公寓》,奥斯特尔。
赵松:哦,知道。
陈卫:说实话,我还没看过这么罗嗦的语言,不瞒你说,短短的150页,我断断续续看了个把月,而且这是惟一一本在看着看着就睡着的书,以至于我家里人老说它是催眠药。
赵松:呵呵,有意思。
陈卫:但是,奥斯特尔甚至似乎就是为了给“罗嗦”正名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赵松: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陈卫:这么罗嗦的语言,如此容易遭人谩骂的罗嗦,看完,还是觉得他写得太好了,这种好,就我所知的国内作家,没一个能比的。由此再想整个这个新小说新一代,想想他们各自的努力……
赵松: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罗嗦或者简练。主要还得看罗嗦成什么样,简练成什么样。
陈卫:是的,语言的魅力不在于是否精练,艺术的魅力不在于是否语言精练。
赵松:因为那只是表相,不是目的。
陈卫:奥斯特尔,他就是话不好好说,每一个很简单的句子,他都要拆散,也不一定都拆得有道理。但全部看完,还是觉得好,几乎可以说无比之好。当然,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理由了。
赵松:也就是说,文本本身是不是需要那样。
陈卫:对他而言,肯定是需要的,他就是个卑微的人。犹疑的,畏首畏尾但又有所固执的。
赵松:是,他有他的方式,别人没有,这就是他存在的理由。唐僧念经,悟空腾空,各得其所了。
陈卫:他好像在这套书里还有另一篇,我准备看完那篇再做整体思考。
赵松:你说的那个是收在《史前史》那一集里的《野餐》。
陈卫:是,那个还没看。
赵松:我可能要过些时候才能看它们。
陈卫:恩。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们每一篇都有必要看。不会失望的。想想这些译者怎么对待它们,就会觉得有必要看了。
赵松:呵,还有这种念头。
陈卫:恩。因为这几本,你知道吧,你应该也是这样,你会时不时地拿起他们,翻翻,然后又放下,
赵松:是,一直在床头,它们,以及罗伯-格利耶的,西蒙的。
陈卫:心想,也不一定都好吧,以后再说吧。呵呵。事实恰恰是:都好。泰山不是堆的。
赵松:是,火车不是推的。
陈卫:你对他们一无所知,正说明能够有所收获。
赵松:他们可能更像药引子,如果你手中没料,他们是没用的。
陈卫:哦,这个我就不知道别人了。反正,夏天一过,也就是《定淮门》和《宽躺椅》一完,我突然,一下子,真奇怪,我感到我可以完全摆脱过去了。也谈不上“摆脱”,因为一直以来我也没有以“摆脱过去”为目的。我的意思是:我一下子突然可以和过去没关系了。我可以一切从头开始了。我可以不要过去已经写的一切了。就是这感觉。我感到:我现在真正开始写作。
赵松:一年多以前吧,你气势十足地声称要写长篇,我知道你会写,可能也一直在写,但我感觉,你可能还会等些时候,才能完成这个愿望。
陈卫:前面,怎么说呢,是长身体吧。
赵松:这就像一场演出,报幕的说,下一曲,第十七交响曲,而后你却突然来两个小回旋曲。
陈卫:长篇,诶,怎么说呢,长不长短不短的,真没那么重要。如果不想写,或预感写不好,干吗一定要去写呢。目的是好,而不是长短。问题是要感到那需要。要感到长篇的来临能改变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身体。
赵松:这种感觉非常好,更自然了。
陈卫:一年到头,这么多人在写,字倒下来把地球也压扁。不缺这一两个长篇。慢慢来吧。写作和生活是相伴的。这一切,都会顺其自然的。天天在写,就行了,忘了篇幅。说不定,我就正在写长篇呢。不要那么多重大的计划了。
赵松:我看过你的受奖词之后,感觉你更像个哲学家,虽然你一向不喜欢涉及哲学。
陈卫:是么?我前一阵子在看点哲学。不过这与受奖词毫无关系喽。我觉得无所谓哲学家不哲学家的。比哲学家更重要的是,哲学气质。
赵松:因为你谈到的是一些比较本质的问题,当然也是大略谈及的。
陈卫:哲学气质有可能与哲学专业毫无关系。
赵松:是。我对照地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受奖词和以前的一个文章《清算与对立》。
陈卫:我肯定没有精力专门去学习哲学专业了——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以前所谓没有兴趣,我估计也是因为感到没有精力才找了个这样的托词。
赵松:“清算的同时无法免除同情,忏悔的同时无法抑制享乐的美妙:矛盾正是真实和丰富的本原。”这是后者的结尾句子。
陈卫:哦,这倒是我对《窄门》和《背德者》的真实感受。
赵松:对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呢。
陈卫:这句与我亲身感受无关,我可以保证。只是我对两作品的理解而已。我想我自己还并没对自己苛刻到那么深。没到清算和忏悔的地步。
赵松:“人活到一定年岁之后会盼望自己更成人一点,更老年一点,更符合他的年龄应该出现的成熟和宽厚,因为更真实的状态是模糊,而不是清晰。”这个更符合你的心态吧。
陈卫:这也只能作为盼望了。至于做到,还需要日后再说,呵呵。
赵松:嗯,是需要日后。你的那篇关于纪德的文章写于零三年年底……
陈卫:其实,我觉得我变化不大。
赵松: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卫:基本上在一条路上走着。比较清楚自己的轨迹。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不意味着没变化。而是这变化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或者说,预期之中。当然,并不是把握十足,所以也并不是毫无乐趣。主要是没有什么改变我的大因素,基本上没有。还是比较稳定的,不存在大起大落。
赵松:嗯,一种缓慢的变化吧。
陈卫:是的。然后,突然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大的飞跃,属于预期之中的顿悟。
赵松:就像打开一扇窗?空气流动,清爽无比?
陈卫:好像是这样:觉得它迟早会来的,那它就慢慢来了,有时它来了,觉得它还不应该来,所以还会拒绝一下,故意去走一下弯路,然后,就突然来了,突然来的时候觉得很好,那就来吧。应该的。而且这来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更大更多的来还要来。慢慢地,来到死吧。
赵松: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年的感觉?
陈卫:成年,恩,我肯定成年了。越来越感到。不希望自己再有年少情结了。不过成年与目力浑浊又无关喽。
赵松:嘿嘿,视野更开阔了,甚至能看到大地的尽头。是不是容易产生类似于宿命的感觉呢?
陈卫:没有没有。我只觉得自己要更沉下去。更没什么声音。因为世界太大了。人太小了。至于宿命,不想了。我们生下来就宿命了。我们只有不想宿命时,我们才活在生命里。宿命是头和尾之外的事,生命是过程中的事。简单地说:就是盯着现在,活。
赵松:嗯,这话说的挺通透的。
陈卫:反正人说到底是没什么意义的。比强比弱都没意义。我们只是要在这无意义之中珍惜而已。
赵松:那今天的黑蓝对于你又意味着什么呢?
陈卫:珍惜今天嘛。
赵松:好像今天你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拿得起放得下了,对黑蓝。它只是你生活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必须要怎么样的事儿。
陈卫:因为我想通了一件事:做黑蓝,只是我和朋友们的需要。其他的,都太次要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用。而我们自己需要,什么也毁不了它。没有黑蓝,还会有别的东西,而不再是必须怎么样了。再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它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很多人在这里度过时日,它并不属于一个人了。它只要没变质,那它就是鲜活的。
赵松:重要的是鲜活,而不是别的什么?
陈卫:我惟一的任务就是使它不变质。其他的都是野心。
赵松:就像你的作品?
陈卫:我想,我们的生活总得有些东西相伴。写作,黑蓝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类。
赵松:对于同时代人的写作你还关心么?
陈卫:他们和我们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