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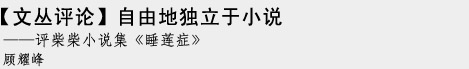
1987年出生的柴柴(张捷)有可能是21世纪中国第一位成为“神话”的小说作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柴柴对小说理解的高度、对小说把握的才能放到历史层面,在这个年纪与她相提并论的也许是这些名字:拜伦、雪莱、兰波……有一个词在当下已经被用得泛滥了:少年天才。因此用这个词,在当下,甚至有些侮辱她的才华和实际才能。
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发展至今,毫无疑问,它已经不再是盛载道德、描摹理想、反映现实、技术拼接的工具。小说越来越逼近于使之成立的最初元素:语言。倘若我们简单而通俗地把小说比喻成一座房子,那语言就是其中的砖瓦。砖瓦的实用性与小说语言表达上的准确性相仿;砖瓦本身的纹理与小说语言色彩相仿;砖瓦的构建与小说语言的整合相仿。柴柴的小说语言,正以一种貌似“不准确”的“准确”,以绕开中心纠缠外围进而凸显主旨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呈现了表达上的“准确”。而在这过程中,她的语言恰如一丛有自己生命力的丛林,自由而有序地繁衍、生长,带给作品一种全新的五彩缤纷——然而其中暗含秩序。这样一来,柴柴小说的语言本身也获得了生命。因而,即便脱离了小说本身,她的语言也有足够的力量得到成立——尽管它们从未脱离过。在这个意义上,柴柴的小说,无疑正是对当下小说本体的一种无意识、但却极为有效的革新。
柴柴的小说集《睡莲症》,正是这样一种景象的集中体现。你无法预先感知那些出彩的意象从何而来、去向哪里,也难以想像,那些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在她的笔下怎么就充满了奇怪而自由的光晕。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这些意象和光晕,在她的小说里又都显得那么自然,丝毫没有吃力、做作的痕迹。在当代,喜欢“奇异”、喜欢“出奇”的小说作者大有人在,而那种使边缘化的词汇、感觉自然呈现,从而使它们自然、自由地独立于小说本体,柴柴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可能柴柴先天具备了这样一种不为人知、甚至自己也并未自知的能力:她无视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却又能把“叙事”的效果完好呈现。说她无视,并不是说没有想过要尝试,只是,从这本书的诸多作品里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对她是无效的。往往在写的过程中,她起先是想老实走在传统叙述的道路上,但随即又呼啦呼啦转换了方向,呈现了自己的天赋。这样说也许会有一个错觉:小说有几种互不相合的语境存在。事实上却不,在整体效果上,最初的那些尝试,也被自然而贴切地溶进了她的那套方式中,就好像一个功能强大的胃,把属于她的、不属于她的东西,一起消化。
要是我们把天赋、才华当作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使用,那人人都拥有天赋、才华。但这样的“客观”放在柴柴身上是不合适的。她拥有着与众不同的、亮丽的(我以为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天赋和才华。如果我们心存善心的话,就唯独要希望:柴柴能把这天赋和才华燃烧得再持久一点、再绚烂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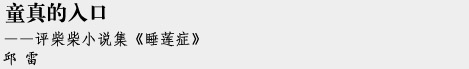
逐字读完柴柴的中短篇小说集《睡莲症》,我心里有个信念越发坚定:柴柴在19岁之前写下的这些作品,足以使任何一个还存有些许童真的人感到震撼,哪怕他/她已经被超速的现代生活拖得疲惫不堪、眼袋肿胀、肉质松弛……
我并不是要强调这本小说集里显现出来的童真,不管是她对世界的把握方式,还是语言上的特征,都不是“童真”两个字就能概括的,对柴柴来说,对每一个从最本真的意义去理解文学和小说的读者来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强调。因此,“童真”两字对《睡莲症》来说,仅仅是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一个进入新奇但可信的世界的入口。在这个入口里面,有带着一丝焦灼的小姑娘急于逃离含糊的肉欲的迷宫,在一把玩具锁上碰运气(《霹雳火》),有饲养着种种奇怪虫子的器官地牢(《虫宫》),有入院的老人静静体味与家人的距离感,在缓慢的时光中种植鸦片(《睡莲症》),还有皮蠧、眼睛壁虎和需要蘸着汗水吃的蔷薇……
这么说的话,她只不过是在记叙每一个小女孩都会有的奇思怪想喽?不,完全不是。柴柴的小说虽然包含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经验的事务、事件,但它们并不是无法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时刻都在激发我们的理解力,为呆板的日常生活提供更丰富的、活泼的和更具意味的形式。小说里人与物的奇怪的名字也好,令人讶异的场景和事情也好,陌生而新鲜的情感体验也好,都还是对现实生活图景的描述,不过是变了外形的,经过裁剪与重组的。这就使我可以肯定:阅读《睡莲症》不会是费解、难捱的,而是新奇和愉悦的体验。
比之“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几乎人人都会想到的问题,《睡莲症》这本中短篇小说集更多地体现了对“可能的世界有多少种”这个问题的偏爱。这自然是一类更开放的心灵的领地,在它们身上不存在遭遇异己时常有的焦虑感,它们需要面对的不是自身以外的任何压力,哪怕这种压力仅仅作为变了形的对象在作品中存在,也不会唤起任何道德上的、社会意义上的同情。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不需要同情。
所以柴柴的探究方式是主动的,但并不激烈,她超越年龄的细腻、沉稳和耐心为之作出了保证。在《睡莲症》里你不会发现年轻人中常见的对生活的、对社会的甚至对自己的不满;你不会看到急迫地要表达一些看法、想要使读者惊讶的愣头青式的语言。对比很多作家被小说以外的动机引诱、牵制、逼迫而写出不是小说的小说,柴柴将艺术的光亮置于作品的核心,而让它辐射到小说的每个角落。
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事件序列,尽管在时间上从来都只有单一的向度,却总是能使我们相信(乃至虚构)它的丰富、它的多面与多向、它的回环反复,借助记忆或者对记忆的重构,呈现出一个个隐秘地关联着的,递延的或者交汇的场景。如何将它们置于叙事链条之上,柴柴从来都不完全依赖现实的逻辑,它包含了欲望、动机、想象……当然了,它们让事件和场景显得色彩斑斓,也让小说对感官的刺激更猛烈持久,尤其是她的小说里那些或者直接通透的、或者闪转腾挪的、种种花样翻新的意象:话痨腺、充满水的冬瓜、暗和软的巨鲸的胃部。仅仅说它们表达、表现了某种不同的趣味,还远远不够,这些浑然天成的修辞,毫不费力地展示了独具品格的心灵是如何与这世界碰撞和摩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