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小说的作者擅长夜以继日地批量生产他们的产品,并在这些产品获得的物质及虚荣中自豪;而艺术品的价值却在于其创造过程的卑微、沉痛,以及她奇妙的偶然性和唯一性。目录中的这些小说是洪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创作的风格完全不同的十部作品。尽管她们不能全权代表洪洋小说创作的全部,但毕竟通过一个个不同反响的局部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将生活与想象转化为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文艺作品的能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所具备的文学天赋与故事天才。
在这里我不想逐一评论这十篇小说,也无意花太多笔墨讨论作者的生活。我只笼统地画一张速写吧,关于洪洋的作品和洪洋这个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就像里尔克笔下的“浪子”,一个为了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为了逃避太多的甜蜜、安稳、富足与被爱,为了寻找那只存在于精神中的爱尔弥德花园而放逐自己的青年。怀着一种看似落伍的、不合时宜的、被这个时代所嗤之以鼻的英雄主义情结。
一般而言,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折中主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使自己的作品严格地聚焦于一个观念,一个能够点燃其激情的主题,一个他毕生探求不断有精彩创新的主题。例如,海明威便痴迷于如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在他目睹了父亲的自杀之后,这一问题成为他的作品的、乃至生活的中心主题。他在战场上、在体育运动中、在猎场上,不断地追逐死亡,直到最后,他将猎枪插入自己口中之后,才终于找到死亡。查尔斯?狄更斯的父亲因债务诉讼被捕入狱,他在《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和《远大前程》中反复地描写了孤独的儿童苦苦地寻找失散的父亲这一情节。莫里哀对17世纪法国的愚蠢和堕落痛恨不已,其作品的题目读起来就像是一份对人性恶的诉状:《吝啬鬼》、《愤世嫉俗》、《没病找病》。这些作家都找到了他们的主题,并支撑着他们走过创作的漫长旅程。
在这一点上洪洋似乎是个例外。为了追求技艺的提高,在手法及内容上的不断尝试使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出行,成为一场场未可知的冒险。这种好似命运般诡谲的不确定性就像他难以固定的读者群。因为作为读者,我们似乎很难跟上他的步伐,刚刚适应了一篇充满阅读障碍的、晦涩得像诗一般的小说,他可能转手就写了一篇语气清爽、通俗易懂的童话。刚刚在讲述古代皇宫里的太监和宫女,另一个故事却给我们描绘了一帮看似被时代所抛弃的青年的无所事事……“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大概是我对他及他的小说最主要的感受。
洪洋写小说的手法很自由。与之相对立的应该是那些擅长(更确切地说是只会)讲述刻板故事的作家们的行文风格。刻板故事的作者永远没有意识到,生活事实是中性的。试图把所有事件都包罗在故事内的最脆弱的借口是:“可是这确实发生过。”任何事都会发生;任何可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实际上,不可想象的事也会发生。但故事并不是实际中的生活。纯粹罗列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决不可能将我们导向生活的真谛。实际发生的事件只是事实,而不是真理。真理是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思考。
小说美学是表达活生生的故事内容的手段,其本身却不能成为目的。
所以洪洋是聪明的,在他的作品里没有陈旧的格式化小说套路,没有荒唐的所谓畅销小说模式,没有新书上架中那些我们早已不忍卒读的陈词滥调、悲情、颓废,以及已然成为发笑酵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或是中年妇女的幽怨和无病呻吟。而是智慧、诗意、充满幽默感的叙述,在这个愈加娱乐化的时代为我们保留着一份独善其身的冷静。作为一个叙述者,他在必要的旁观中获得的一个个富有意味的细节,使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若有所思。一种自觉的写作中的狡黠以及个人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并完善了陈旧的艺术形式。
一个写小说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韵律的诗。洪洋和他的小说早已带着其完善而不动声色的张力置身其中。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创造性地将所看所想转化为一种更具表现力的更好的形式,生动地描述世界并捕捉人性的声音。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一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如此精心而富有创建地将经典形式揉碎和弯曲,我如此理解洪洋小说中潜藏在小情节中的内心生活,如此乐于接受其间那反情节的冷酷彻底。

以读者的身份去面对洪洋的作品,我们似乎不能避免地会被“触动”。在大众文化批量化生产的背景下,在情感模式可复制传播且显得日益廉价、麻木的时代里,作为个体所拥有的情感体验显得稀少而珍贵。然而对于一件创造性的作品,能否唤起受众的情感——感动、振奋,甚至愤怒、失落——仍然是我们衡量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这触动读者感情的整个体系,落到写作者洪洋身上,似乎又与他自身的个性分不开(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个有趣又严肃的话题)。洪洋的敏感、对世界的好奇心,在一个不断行走的状态中,使他时刻保持着倾听的姿态(有时甚至是窃听者),进入他目光的人与物更是囊括了包括“我”在内的整个世界。他探究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宽广进而宽厚的视角仰赖作者的耐心和勤奋,逐渐内化为一种自然、自发、持续的才能,它为作者塑造,更塑造了作者,“他发送文字如同发送触须,伸向世界漏水透风、色彩斑斓的物质。”(卡尔维诺评价弗朗索瓦·蓬热)——这种触角早已长在了洪洋体内。
优秀的作者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经营自身的禀赋,抛光打磨以至宛若天成,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本的潜在结构在向内和向外两种维度上同时展开:“走路就是为了坐在窗前,看一团团水和空气弃我而去。”(《不过是OPEN》)——最终,洪洋成为这样一个既热情又沉静的观察者,目光退后,自身内陷,这种内陷打造出的文字世界又与宽广的真实世界的纹理产生了奇妙的吻合,就像宇宙中的虫洞,构筑起两类视界之间的管道。
探究一个作者的人格与他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个有趣的话题,我不由得再次提及这一点。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写作的态度,其写作的纯度,和他在写作中将抵达何处的可能性等等答案。洪洋自身人格与写作之间的吻合,揭示了他小说的复杂性(即“宽厚”),他不是端坐云端尽叹世间美好,也不是以愤怒的姿态尽数社会黑暗,他一视同仁。就像他所爱戴的纪德说的那样:“一个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才表现出坦诚。”这同样决定了他作品中的抒情的质地——它不廉价,也并非轻易得来;它直指人心,无所畏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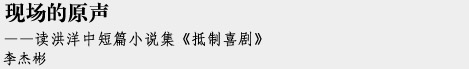
无论从语言还有情节,洪洋是一个典形淡妆者,很少用浓烈,复杂的手法去刻划故,所以有如沐春风的舒服。他的小说与其说有贵族色彩倒不如说他有一种诗人气质,他的某些语言,意境有着诗歌的优美和迷幻。
《抵制喜剧》是个很黑色幽默的词组,同时也是句不错的响亮而奇怪的口号。拿它做书名再好不过了。这本书,是一本有关“旅程”的书。出发、到达、居住、离开贯穿其中,同时有孤独得让人觉得冷酷的精神力量。如他在《不过是Open》中所说“尽量不让自己找到同伴,保持缄默,保存命运中最愚蠢的部分”。洪洋擅长借用小说叙述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人的灵魂,写他的等待、迷惘、老去,甚至一口气追溯到时间本身去。
洪洋对语言很着迷,这种着迷不是指对制词的苛求,而是对词语的各种属性的探索。这使得他的语言深刻独到而有些霸气,感染力很强,而且具有诗性,这可能和他早期写诗有关。《镜框迷面》里很多的句子就是这样的,比如王丹的神秘和他不断重复的: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时的场景就有着诗歌的现实与迷幻的双重张力,让有人突然一振的感觉。世界在他的眼中,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诗意的,同时也是荒诞的。在这种两极中我们似乎可以思索:诗意或许就是荒诞。
《抵制喜剧》里作者本人对社会某些阴暗面的描写如些生活,很多东西不是不为人知,而是你根本无法去面对它。在小说中,洪洋写了一个男人,写他的全部耻辱,一个受过教育,不甘于堕落,又毫无立场的男人。无论是他从事的工作、他所受到的对待以及在他身上遭遇的爱情,都带给他耻辱。洪洋没有对这个男人产生悲悯之心,也没有刻意丢弃一个男人的尊严。他做的就是还原这一切,让人看到耻辱的诞生,看着人如何被钉在社会之中。让人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的是,在这种我们所处的耻辱的中心,我们似乎无法拒绝无法逃避甚至很依恋。《不过是open》里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作者通过接人,旅途,(火车和汽车,等车)现出了十数个场景,并都作了精致的描写,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犹如置身一处曲折的山水,山穷水尽疑无路,花明柳暗又一村。衔接之处足见其妙。《内,充公》里作者以一种缓慢,而又鲜活的语言,以像记日记一样精准的方式记述了十来天发生在生活里的小故事,他几乎是不作任何艺术加工。语气里可以读出长途跋涉者的疲倦,久别重逢的激动。人物栩栩,性情皆从事中露,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故事。它没有什么内在深度,也不会有什么浅薄陈腐,他就是一种现场的原声。
黑天才的小说已经越来越丰满到位了,越来越珠圆玉润,及人之所不能及。这几年他用不断的自我完善哲学观来表达或描写我们这个无聊的社会的现场。当然这并不是黑天才的高峰,这只是他的一座小山。他能写得更好,他将写得更好,因为现代艺术就是个人的不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