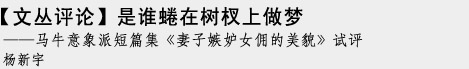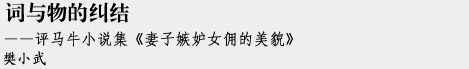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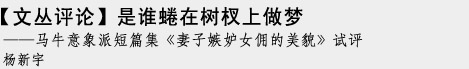
朋友极力向我推荐马牛的短篇小说集《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称这些极富想象力的极短篇特别适合我这个对小说已极度失望的人阅读。我在预想中便期待着看到一位布扎蒂、埃梅、星新一这些短篇小说之王在中国的徒子徒孙,翻开书页,许多小说甚至短得超乎我的想象,我大喜过望,但读完之后却令我大跌眼镜,包裹在布扎蒂们超拔的想象力之下的仍是些精巧、奇诡的事件,但马牛的小说可以是诗的,视觉的,行为艺术的,甚至是肉体的,但绝不是小说的,他的小说中即使有事件,也是断裂不成片段的,即使偶尔不断裂,也是毫无逻辑可言的。这使我想到,“马牛”一定是个笔名,可能来自“风马牛不相及”,肯定不是来自“莫为儿孙作马牛”。
我们这个时代绝无可能产生文学大师,这是一个超稳定而又极度平庸的时代,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千篇一律,上学、恋爱、工作、结婚,最多还有些婚外恋、同性恋,70后作家如卫慧之流只能书写自己的身体秘史,或许并非他们特别热衷此道,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把握到的真实,80后不说也罢,免得被他们骂。1977年出生的马牛自然也不能外,他的小说是独一无二的,看不出对大师技巧的借鉴,但同时也是典型学院派的,马牛同样欠缺丰富的人生体验,也没有编造故事的能力,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科班出身,使他过度耽溺于意象之癖。读马牛的小说最易联想到的是海子的《初恋》、《木船》以及孙甘露的小说,同样依赖诗化达到反小说的效果,但海子的神秘气息可以感受,孙甘露的意象经营整饬、纯净,工于匠心,而马牛显得更为独特,完全依赖灵性写作,光怪陆离的意象层出不穷,完全不加修饰甚至不加节制地管涌。“你永远不知到他会从哪里翻出一片垃圾,用絮絮叨叨的语言把它清洗干净,打磨光滑,回顾它的来历,秘语它的传奇。”(马牛:《宋的城堡》)神秘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不足以描摹它的风格,我姑且名之曰:意象派短篇。“意象派”自然应该很短,似乎也只适合诗歌,庞德的名篇《在地铁车站》就只有两句,而马牛的小说尽管很短,但密集的意象,却加大了小说的密度,如同度数很高的浓缩酒精,一次就足以让读者“心醉神迷”。
小说集以短篇《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为名,或许出于市场的考虑,因为这篇小说是最不晦涩的一篇,且光从名字就可以读出“性、欲望、故事”,颇能吸引人的眼球。因为马牛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私人的宇宙,那些随意出没的“远远取譬”的意象,诡谲多姿,但作者并不提供读者进入其意象体系的线索,读者只能远观其私人宇宙的富丽堂皇,却无由亵玩其堂奥。于是我们只有借助他相对好懂的小说,寻索深入其小说的可能性。《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曾被编入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K文件·1不用麻药的请举手》一书,这是一本汇聚网络有趣图片、文字的解颐之书,多数作品带有恶搞的气质,可见这篇小说在网络中是颇有知名度的。的确,《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具有这样的“K文化”特点,荒诞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涂抹了一个表现人性嫉妒的故事,然而妻子因嫉妒女佣的美貌,而采用的将女佣暴露在外的身体包起来、套起来的做法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女佣的“美并没有为此减少一分一豪”,因为她似乎“已经美到需要把身体保护起来的程度”了,“别人眼睛都亮在外面让人看”,女佣的眼睛“却像一个性器官似的被遮蔽着”。的确,“只有当裸露和遮盖的冲突出现而无法消除的时候,色情才会发生。”(余虹:《审美文化的世俗化流变》,《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这样突转的效果的确是网络文化所乐于接受的,而又绝无晦涩之处。这篇小说中强烈的感官性,对身体的敏感,对性的隐蔽表达,在马牛其它更为意象化的作品中同样表现出来,只是表现得更加隐秘。
《新寡妇之夜》中新寡妇的所作所为便比《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中的妻子要难于理解,“她用胶带把左眼贴住,戴上墨镜;用棉花把左鼻孔堵死;用红泥把左耳孔泥住;用黑绷带把左臂左大腿缠得密不透风;用细长的铁丝把左脚的脚趾一只只细细捆扎;头发一半全部剃光,另一半有时辫成辫子垂在右肩,有时塞进帽子”。然而因为《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的存在,我们便能理解马牛对身体能量放大镜般的敏感,对一半身体的捆绑和遮蔽抑或修饰,带来难抑的颓废气息,看似压抑了身体欲望,塑造了寡居的贞洁形象,实质上,如真的贞洁又何须压抑,而对身体局部的指事式的标注,恰恰成为色情的展示。马牛对性、身体的颓废、绝望式展现分布于他的多数篇章中,皮肉、骨头之类的意象大量出现。《七刀》也是特别精致的一篇易懂作品,写人被时间安排,在马牛笔下,人,表现为他的皮肉,骨头,身体,不停地为秒刀、分刀、时刀、日刀、月刀、年刀、生刀所砍杀。《七刀》给别人可能会写成一篇哲理美文,但马牛在《七刀》中却以简洁的方式解剖了自己钟爱的两个主要意象:身体和时间。而身体,有时候被马牛提升为生命,有时候又加以物质化,如《两个字的书中岁月》及《我的玫瑰试验》中的雌雄玫瑰,而它们总在时间的无情鞭策下,发生着异化,被时间击败,挣脱不了自我的束缚,成为物的奴隶。如《链条女》,“把链条缠在身上,想像自己是架什么机器,工作机器、吃饭机器、睡觉机器、做爱机器……”,“她开始她的机器生活。她把那个温暖柔软的自己隐藏起来,藏到冰凉的机器后面”。而《标签女》则“把自己藏在标签后面,不让人发现”,“始终没有被探索被发现的乐趣”。《远道而来的客人》忘了自己国家的语言,忘记了回家的路线,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依然住在我们的城里,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分别了”,尽管他们还是从不出门。而《一则外乡人的故事》中外乡人起初试图唤醒树枝上沉睡的村民,最后自己也找了一棵满意的树,信心十足地爬了上去,而沉睡似乎象征着死亡。《亲爱的肉》让人想起电影台词“跟着你,有肉吃”,“你就是靠着这些肉,邀我与你度日”,我起初并不想用月季和你交换肉,爱情与物质不可交换,但我也有肉食的需要,不能不屈服于这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最终我也像动物一样被你的鞭子赶进绞肉机,成为一堆跳动不已的肉。而《这个农夫爱杂草》中农夫竟然“无法接受没有杂草的菜地”。
由于拒绝读者轻易地进入其私人宇宙,马牛便成为他所创造的意象的唯一主宰,这些意象“灵验不灵验”完全由作者主观操控。“城堡里的第一尾鱼在某堵墙的水草中诞生了”、“玫瑰试验”、“图形云朵”之类以神秘主义面貌出现的带有童话一般品性的意象俯手可拾,能指焕发出熠熠光辉,甚至带来影像般的梦幻节奏,然而它的所指又是极其飘渺的,正如张炎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断。”每一个意象如同珍珠一样炫目,但作者却不给你串珍珠的线,而这些珍珠一样的童话因子,由于串不成串,不可能达到童话诗人如顾城早期诗作那样虽不可确解,但仍清澈纯净的效果,看起来更像一个精神谵妄症患者的呓语狂言,恰如顾城后期诗作已拒绝别人理解的晦涩一般。由于马牛创造者的角色,他对意象群体的精细描摹带给读者更多的感受颤动,马牛纯意象的作品如《沙粒上的爱情》、《我的玫瑰试验》、《是谁蜷在树杈上做梦》等,创造了沙粒、玫瑰、自转的树叶等纯粹的意象,能够带给读者比较纯粹的诗意感受,《八月意象集》里不断渗透的意象更使这种纯粹性升华。而那些下定义式的判断,则显得比较生硬,如《革命的腰最美》、《亲爱的,你恨不死蚊子》,既让读者莫名其妙,又易给读者造成心理障碍。“爱一个人就是往嘴里塞东西”之类的表述也显得毫无意义,既是反小说的,也是反诗的。《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七刀》、《亲爱的肉》、《神的循环》、《城里的皮屑》等篇则是逻辑性较强的篇章,是真正意义上有意有象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多,更多的则有丰腴的象而无意,难免故弄玄虚之嫌。
马牛清楚地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也坦言是因为“觉得诗歌太短,写诗不过瘾才开始写小说”的,而他的小说也正是“拉长了写的诗歌”。因而,马牛的多篇小说对于小说或书甚至虚构本身进行了探讨,如《》、《羊皮书》、《泪之书》、《子虚乌有的大师》、《蚯蚓巷臆想书》等,这些他想像中的书,肯定也寄予了对自己创作的希望。《》是一本给“少数富于冒险精神的读者”无限次数,以无数方法阅读的书,如果说马牛描摹出的这样一本可以横读竖读的书,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话,那么《泪之书》更像是他自己创作的写照,“这根本不是一本让我阅读的书”,“这本书首先寻找的是精通光影变化、精通乐理的读者”,“整本书的每个泪形文字在不同的光线下,都会散发不同光芒,光芒不同带出节奏的不同,节奏的不同又使得每一行、每一段、每一页不期然地演变为一支光的交响乐”,因为这本书“发出的邀请直接针对身体:来吧,感受,只需要感受”,它提供的不是故事,而是“舒展、紧促、顽皮、哀伤、惶然、月光下的呜咽”这些纯粹的无法具象化的节奏。另一方面,马牛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讨厌它的书和书里纷乱繁杂的梦”、“我也不会拿起书读这些莫名其妙的字”这样的句子,很像是他的自嘲。剖析诗歌有毁坏美的危险,剖析诗歌化的小说同样是危险的,不知我挦扯到的这根线索是否虚幻的。
马牛的这些意象派短篇,注定是小众的,但还是值得向感受性强的读得下去诗歌的读者推荐,疯癫的意象带来肉体般的感受,进而上升为灵魂的呼应,这是阅读马牛小说带来的快感所在。这部书,是需要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去阅读的,因为这些意象的烈酒,一次饮得太多,会令人恍惚而抓狂,我知道我还会无数次地去翻阅它,用它唤醒肉体的感觉。真的应该特别感谢黑蓝文丛,在泡沫文学泛滥的时代竟有如此魄力,去出版“十数年来在中国一直处于低谷”、没有什么市场的中、短篇小说集,尤其像马牛的本来只能存在于网络中的意象派短篇,这几乎是一本不可能被出版的书,马牛本人就说“把它当成无法出版的小说去写的”,现在读者能够读到它,真的是一种幸运,尽管它还显出生硬与青涩。当然,马牛这种过于自足的写作方式,不仅晦涩,也妨碍对生命体验的深度开掘,如果能够继续保持意象丰盈的想像力,又能够在跳跃的意象间架起引渡的桥梁,并不会降低小说的先锋性,却能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所以觉得马牛的小说之一《是谁蜷在树杈上做梦》恰是他创作态度的写照,故而引用它作为这篇评论的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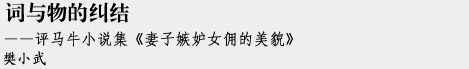
在《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里,那些粉碎并且重新搅和的物、关于虚构的虚构和文本的走马灯式的意象呈现再一次令人恍惚。马牛的小说有着难以描述的独特气息,那是穷尽技巧或者吸取大师的经验无法做到的,这些独特的气息来自于马牛骨子里的意象癖。请放心,马牛很少用意象给读者制造语句障碍。阅读马牛的小说并不会感到需要在古怪艰难的词句组合之间寻求解释得通的理解方式。小说中的意象虽然复杂繁多,但不会有割裂感,它们流畅而抒情,就像《沙粒上的爱情》里的主人从一个细小的沙粒跳到另一个沙粒一样,阅读马牛的小说是一次有惊无险的词语跳跃,下一个词儿永远是未知数,只不过读者通常会估算错误:他以为下一句话会像一朵花那样芳香,却不想走进了繁花遍地——马牛给人的惊讶总是超出预期的那种。那些像用镜子、铁匠、爱人、女巫、士兵制造的文字迷宫让人沉醉于其中,它们像一个完全与现实无干的自我循环的永恒宇宙。
人们很容易被马牛小说中精致的语感和想象力的井喷所折服。然而格外使我迷恋的,是这些意象之间散发出来的诡异的抒情。意象之间的抒情?是的,马牛不是一个冷酷的词语工程师,他的小说里经常缠绕着两个角色之间的戏剧。《革命的腰最美》、《诗人脚下的北欧玫瑰》、《死者的奔跑》……在这些短篇中我们看到了爱情、性、命令与臣服、嫉妒、勾心斗角,作者让它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不存在平淡无奇的宽畅的大路,主人公们必须有着简明而犀利的、独一无二的形象,他们在象征无限的迷宫、森林和沙漠中行走,在镜子和月色中迷失自己,触碰旁人没有碰过的某些事物的边缘。马牛在抒情的表面覆盖了一层闪闪发光的、沙砾一般的词语,于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迷人气息开始显现。在《新寡妇之夜》里马牛小心翼翼地储藏好一切可供抒情的部分:“她用胶带把左眼贴住,戴上墨镜;用棉花把左鼻孔堵死;用红泥把左耳孔泥住;用黑绷带把左臂左大腿缠得密不透风;用细长的铁丝把左脚的脚趾一只只细细捆扎;头发,一半全部剃光,另一半有时辫成辫子垂在右肩,有时塞进帽子;……”这是一种对欲望的精心保存和修饰,一种表面贞节却暗流汹涌的最为淫荡的色情展示。马牛放大了身体局部的性感,用捆绑的布和绳索修饰它们,他的抒情始终发生在细节的针尖之上。人们用物和身体,用行动的细节互相问好抑或交恶,物体被抛光,显示出陌生的、无法命名的特质,然后开始被作者迷恋,而人们只有扮演了某种职业才能被作者叫出名字——这样,一种原始的,童话一般的小说品性被马牛打磨了出来,这完全是马牛的独创招数,我们阅读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马牛印记,永远不会和别的作者混淆。
关于物,马牛走得更远。在《七刀》、《两个字的书中岁月》、《死者的奔跑》这样的小说中,他让时间和生命的运动流转附着在物体之上以便叙述,兵行诡道的寓言绕开了书写的沉重感——那是马牛极力避免的感觉,而在《城里的皮屑》,《城外的月光》、《八月意象集》中,物体的存在感和词语的轻盈虚无之间的摩擦被研磨到了极致,似乎读者的手指一抽搐,那些精心布置的景象就会粉碎,不复存在。对物的迷恋延伸到了对于文字、词语、书的热爱,于是,马牛的抒情进入了词语的内部。《八月意象集》里的水手不再靠岸,而船长在海上放映电影,卖花的姑娘切下了一片花茎切面——这是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悲欢离合,芹菜不是芹菜,刺客也不是刺客,他们只是词语的晶莹碎片里反射出来的残影,人们只需要拥有词语本身就已足够。
因此,马牛对关于虚构的虚构总是乐此不疲。他写下了《》、《羊皮书》《泪之书》、《子虚乌有的大师》,我喜欢马牛的这些想法,一本书可以被无限次数的阅读,另一本乃是用眼泪制成,那些作者们总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奇特理由让一本书出现在世界上。这是关于书中之书,作者中的作者,词中之词的写作。我本可以说得更多,但这些干巴巴的评语,远没有一次阅读更为有趣,这是一次文本的碎片折射意象的无限实验,一次在语言的金黄玉米地里的穿行,是马牛独有的词与物的纠结。

《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是马牛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目录显示的三十三篇,读下来则大大超出这一范围。如《》所述,并不能穷尽自我和除此之外的任何一个阅读者。
时值凌晨,我仍然不能从阅读中脱离出来。眼下要写的这些东西万万不能错了自己的面目,我真诚地说出我的阅读,那在一定程度上会损毁这种快感,本来是自己内部的东西可要承受歉意并且责任,还是要说出来。我更愿意赞同七月人的看法,阅读马牛根本就是一种惬意得进入,能得到多少完全依赖个人的感受力。小说也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我私下用了惬意,别的什么形容词都好,我有意模糊这种感官上的受用,难以表达,只得以阅读来代替所有。
阅读马牛的小说有切实的快感,仿佛有影像的节奏来牵绊你,在这里是一种好意,而非所谓的阅读障碍。不管是以怎样的态度接受下来的,总会在小说中找到你所需要的契合点,于是产生强大的共生感与关联感。在此大概不必强调所言非溢美之词,马牛的小说总能带给人一种奇妙的冲动,其外在的表现是让人的行动发生微妙的偏差,此刻你正是别的什么人,实施另一种意象感极强的行为,他对现实中行之有效的自己发出暗示或直白的干扰,作为自己的那一部分便败下阵来,成为偏差。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里外的,并不能独立于小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魅力。
区别于荒诞的超现实主义成为马牛自我叙述的优势,绕开常规或者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无知的间接侵犯,便可以自主地发展意象或是令意象自主地创造本身。意象对于马牛小说的作用无疑可以与以太对于上世纪的宇宙相媲美。整部书不是在讲故事,而是通过一些险象环生的意象来构成一场庞大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写作者和阅读者双方的,或许并不需要两者相互认同,在任一方实施的主动行为后引发的实时并存的思想,两者皆为是。
阅读不会带来优越感和挫败感,而小说自我优越的来源是有的,只怪作者对于表象描述的做工也精良。在《是谁蜷在树枝上做梦》里看到的对于叶片自转的诗一样的表述携带了太多的韵律,还有意象与生俱来的对写作者思想的模仿,都能让你明白追究最平滑之物的纹理并不徒劳并且有趣。我迟钝的用了描述一词,或许该说是带着谦虚的态度有意靠近表达对象,那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机械性的热爱。要谈爱,要提《亲爱的肉》,爱不作为情感,去爱动物和我都被称为亲爱的肉,漠视生灵的性,拿起鞭子就是全部了。
马牛的意象是绝对直觉性感受,来自器官与非器官。注重意象间的关联,对此又极具立场,不使任一方受到消耗,两者或是几者中都是饱满的。在《是谁》和《诗人脚下的北欧玫瑰》等作品里都可以体会到这种态度。后者是很喜欢的一篇,马牛在其中坦诚了自己直来直往的幽默(《亲爱的,你恨不死蚊子》也是),那个失去支配目睹和愉悦的波斯剑客也是中意的形象。小说中出场人物很多,可以看出,人、论述人、需求性自体模糊的人对于马牛都是完全不同的意象转化。他是善于分解细微差别的,一如在《七刀》与《两个字的书中岁月》中对时间人生技巧性很强的解析,仿佛分拆机械钟表的零件,人是在修剪这段时光同时自我消长。马牛做的是将岁月抽离本体再重新放回去,倾斜一定的角度,磨合清醒与混沌。另一篇,《一个外乡人的故事》,通过梦境与外界联系,现实则是巨大的障碍,在自我完成中死亡的同类。死亡或生存都还是以生命体为基础来延续,死者延续生者,年轻的死者又追赶老骨头(《死者的奔跑》),思考的目的有时也是为了一幅优质骨架。
马牛小说写作的技巧方面也是相当讲究的。从《革命的腰最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字间的意象渗透,文字作为载体,第一层印象如同一张半透明的纸,通过相似性来完成同一时间的不同叙述,一层一层的渗进去,晕荡开来,影像的模糊程度不动声色的隔离着年代,之间微弱的距离恰好让你用来放置自己的考虑。马牛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也总是能带给人好的感受,暂不论他说了什么,单是那种纯粹表达也能在口腔池塘中循环往复,例如“另一半满是月光的村庄,某个女孩正独自成长为妇人,母亲,祖母,枯骨。”、“一整天,女孩都蜷在这棵植物的上半身,做着自己的梦。傍晚时分,跛足的父亲把梯子架上树干,不平衡地一下一下爬上树杈,捧一只鸟窝一样,把女儿捧回村庄。”、
“经过多年不分昼夜的行进,出发时年轻的死者已经白发苍苍,年老的死者跑光身上新生的皮肉,又开始跑它们各自那把老骨头。”……在阅读小说的同时也被小说阅读着,仿佛有一只柔软的手在触摸你的心脏,然后你会发现,你与马牛的文字彼此相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