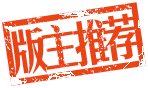我从没叫过她表妹,而是随她的意愿直接叫她李紫官(名字也是有些男儿气),早前还称呼过李紫官同学,后来被她笑话装模作样,遂把同学二字去掉了,我把这看成感情的进步——我时常沉溺在她给我的小喜悦当中。好像每一句话,每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都有温存的鼓励,为我、为这生活凭添了喜乐和力量。与她的相处,我自然是到了格外小心的地步,常为她无心的一句埋怨或是失望,感到万分的沮丧。也怨恨自己不能和她平等的生活,自己处在下风,就故作冷淡的姿态给她看。归乡前给家里的回信也是照旧装作一番少年对女子牵绊的不情愿又必须承担的责任,其实是根本把这视作对自己的犒赏。自登船后,一直在跃跃欲试,想要和她多些亲近的机会,唯一烦闷的是自己预想的潇洒成熟反让自己多落马脚,说话行事,皆不如意,平日的愚笨和无趣也都被放大到竟令自己吃惊的地步。只不便发作,和搬运行李的船夫还吵了几句嘴,幸而被她拉开,又觉得这样的丑态被她看作眼里,更觉得懊恼不已,于是独自一人在甲板上游荡。她似乎也存有其它的心事,凭栏远眺着江岸的景物,我过去陪在一旁,她也是沉默,后来问起我今后的打算,我知道她好论时事,便说,做官好了。她不置可否。
过了东江段,岸上鳞次栉比的屋舍换作了青山绿岱。船上的客人也从客舱出来,到船边看日落,此时红日当头,江面上倒映着如剪影般的婆娑树影,远处可见依稀的人烟,在染红的天色下穿行在寂寥的山水间。船家走到船头来,冲着船客们嚷道,就要到樵屿了。
樵屿三面临江,又近省城,自古船运亨通,熙熙往来。背靠的起伏唤作嬴山,依山势分有一县三镇,县城外是此地最良的杉树林,所以在樵屿,做不得读书人,就理当做一个樵夫,绝不至饿上肚子。人如云泥,也满足于这与世无争、淡泊平静的日子。所以临县时有传闻的地下活动于此却很稀有。直到27年两党决裂,有一伙革命党流窜到此地,引发过一些颇不平静的争端。最难忘的一次,是八年前山上木料厂的几房货物被抗税的山民焚毁,恰好发生在我和李紫官一道回乡的不久前。据说直到现在,从江对岸,还能依稀听到那日山风助长火势,山岚间徐徐火影崩裂的声音。
回来了樵屿,李紫官家里的佣工早早迎候在码头。她和佣工一起把行李搬上马车,也要我一起去她家做客。道理上我也应该先去宗家拜访,当面交付所托。而李紫官也绝非虚情假意,反而是她这样赤诚的热情,让我望而却步。我以要先回家见过父母为由拒绝了。我怎么也不愿这样风尘仆仆的上门,想到那时我竟有上门女婿的自觉,未免还是太过执着的傻气了。最后李紫官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送到了村口。因为我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对我倍加珍视,马车刚近村口,我就在牌楼下面看到父母矗立的身影,不等马车停稳,我先已跳下去,三步并作两步,跑去父母跟前问安。母亲照例是要湿掉眼眶,父亲见了我,觉得我算半个大人了,只捶了捶我的胸口。马车靠近过来,佣工帮忙把我的行李卸下来,父亲见到宗家的大小姐,上前向李紫官打听她令堂的近况。李紫官对我父亲非常恭敬。因我父亲在清末中过举人,后来随新军入主旧王朝的腹心,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手下做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幕僚,在樵屿算是小有名气。兵败返乡虽然消磨了锐气,但还是受到宗族的器重,特别是李紫官的父亲与我父亲是手足相待。
在我父亲说来,我是他的“犬子”,而李紫官在父亲面前说到我,终将我列入了她“表哥”的行列。他们说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生趣、一味的幸福,似乎李紫官也的确适合在我的生活里出入。她不是什么贪慕虚荣、浅薄势力的女人。实话说起来,李紫官没有什么会叫我说个不字,我不知道我对她的痴迷,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佣工甩起马鞭,李紫官坐在马车后面,挥手向我们作别,她明朗的笑容,越远越映射在我的眼前。
我恍惚的多了些可笑的非分之想。
除夕那一日,我在李紫官家帮忙张罗宗族聚会的筵席。唱戏的台子也在县城外的庙口搭建起来。只等到筵席一开,锣鼓喧天,曲辞唱罢,这个年也就风平浪静的过去了。我始料未及的是,李紫宫将她在学校和省城里笃信的那一套,要原原本本的在樵屿上演一次。她这一天早些时候找来了其余几个共同在省城读书的学生,但这件事情直到戏班子开唱才让我得知。
戏码正演到侯方域秦淮初识李香君——李紫官就把我从看戏的人群里叫到了戏台东边的老槐树下,我见到同级的苏姓和杨姓的同学站在那里,他们都比李紫官大两个年级,和我是同辈,但我们的交际并不多,见到李紫官把我叫来也很惊讶。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你不是在开玩笑?”我感到非常不对头,急切地向李紫官发问。
“元孝,这事情我想了很久了,我这次回来也全为了这事。”李紫官一派天真的看着我,眼睛里迸射出兴奋的光亮,真诚的眼神像是能摒除掉世间的所有脏污。好几次我都慑服于李紫官这种纯洁、忠贞的眼神。有一次我还在同学间的辩论中,直接将“革命”说成是“爱情”的同义词。说完我还不无羞怯地,勇敢地看着李紫官的反应,但大家显然都无从知道我未能直抒的心意。这段说辞,只引来不少男同学的奚落,也有女同学将其顺理成章的理解成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那种把肉麻当有趣的革命家。但这次的计划不同以往,和过去发传单,混迹在游行队伍里呼喊口号不同。我们所在不是那个熟悉这种抗争形式的省城,樵屿人怎么来理解李紫官说的“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从他们扎根这里起始,他们的自由就是耕耘这片土地,现在你来解放他们,势必就要为他们找到对立的敌人,谁又是他们的敌人?
“我没有强迫你加入进来,”李紫官扶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边说话,“我们是朋友,瞒着你这件事会让我后悔的,我只是想听听你的话,但我现在不觉得这会起到什么作用,你只管为我们保守秘密,好不好?”
不多时,又有几个人影靠过来,我们停下说话声,静静地目视那几个人影在远处晦暗的灯光下显出人形。
“是谢源他们。”为首的男人小跑着过来,看到我这个生人在这里,又放缓步子,警觉地停在稍远的地方。他手里拿着一卷揉揉皱皱的不知什么东西,看着像一块破布。
“到手了,天亮前也没人会察觉,小野他们还没回来?”
“他们要绕去南门,可能多耽搁了时间。”
“我们不能等太久,戏唱完前都要回去原来的地方,最后敬酒的时候,要让紫官的爸爸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脸。”
谢源把那块“破布”展开,靠近给李紫官看,李紫官抓住一角在指肚上摸了摸,面露难色。
“万一他们根本不在乎呢?这只是些该死的旗子。”李紫官突然不自信的把那块“破布”撇开。
谢源有些恼怒的朝李紫官看了一眼,“我在城头上刷上了标语,天一亮,全县的人都会知道樵屿有我们的队伍在。”
“好,好,”李紫官这时求助似的看了看我,扶住额头,把那面绣有“李”字的蓝底红字旗接了过来,“等小野他们一到,我们就找地方把它烧了。”
谢源点点头,像是突然想到似的,他心怀不满地找到我的位置上下看过来,却是在对李紫官说话:“李元孝是谁带来的?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声,这是让所有人都冒险吗。”我面上一红,被谢源咄咄逼人的架势先压住三分,火气竟没上来。
“元孝不是外人,同学里面他最有见地,在省城的时候,我们谁没被巡捕房的人追过?”
“得!”谢源敲了敲脑袋,一脸愁闷的看着昏黑的夜,过不久转向我说,“那也要看他的态度吧。”
话头抛给了我,几个少年都同时向我投掷来不信任的目光。只有李紫官隐隐有所期待。
我知道再难打消李紫官的主意。又难以忍受让这几个小子捷足先登。心头即刻涌起一阵热血,觉得事已至此,他妈的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对手不过是破烂烂的死物,难道革命的甜头还轮不上樵屿人?
“这样只怕还不够,”我鬼迷心窍,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出了这个主意,“旗子拿到木料厂去烧,顺势再一把火把先前没烧干净的,一次收拾干净。”
几个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想到了前不久山民们引起的那半山的火光,被我莽撞地宣言搞得目瞪口呆,有些人觉得荒唐,直接发出反对的声音。但我像来了兴致,仿佛有生以来头一遭遇到适合我的事业,大言不惭的对他们讲起了这些话。
“上次的大火,还有两个货仓没点着,因为离着木工的屋舍最近,很快火就会扑灭,而且货仓现在也没有货物,遭了不测,也造不成什么损失,充其量是帮忙推倒两座本来就摇摇欲坠的破屋子罢了。”
这是一个释放信号的绝好机会。几个人沉默了一阵,彼此的沉默又相互鼓励,最后就为共谋达成了一致。只是谢源还在冷眼旁观,但他也没有反对,我看出自己有威胁到他在这个团体里的威信,心中暗暗窃喜。
这时候戏台的方向引起一阵骚动。是让人无法忽略的骚动,我们这边也随之浮起些许的不安定,大家或多或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等戏台那里做眼线的人跑过来证实,果然,小野他们被抓住了。
我们看着戏台的方向,宗族里的人喧哗起来,李紫官的父亲把他们安抚住,叫戏班子别停演,他和几个长辈,避开了尚不知情的人群,安排几个手下分头去联系人手了。
李紫官回首冲大家说:“我们只能快点行动了。”
这年春雨来得早,一下就是断断续续的五六天。夜空澄明透亮,新月在枝头荧荧烁烁,林子里的树木还找得到被火烧过的痕迹,那些焦黑的枝干,像是鬼魅附体的巨大阴影,挺立着身躯守卫着山灵的宁静。只有新出的嫩芽,被雨水打湿、洗净,指出条道路,宽容地为我们这些侵入者提供了暂时的平安。排头的谢源高举着火把带路,空气中漂浮着树脂和雨露香甜的气息。木料厂在嬴山相对平坦的后腰上,我们走了大概有一个钟点。终于看到树影遮挡着的,几座宽大的木屋。
“木头是湿的。”谢源举着火把,把货仓照亮。
我们只能试着找了些干草堆到货仓边上,待到干草烧尽,全是用原木构造的货仓依旧不为所动,只匆匆烧黑了一些皮毛。大家都好似被什么无情的嘲笑着,陷入了被戏弄的焦躁的沉默中。山下此时可见到影影绰绰的人影,还有那些手举的火把在慢慢地移动。
“他们上来了。”
“他们怎么能知道……”
“可能只是没头苍蝇的在找,是这里的目标太大了。”
想到有可能被抓住,众人事先激起的热情,瞬间就被恐慌替代了。不知道是谁想到了后路,开口说:
“房子烧不起来,我看干脆旗子也不要烧了,我们给藏起来,事后留作他用。”
李紫官反唇相讥,她把旗子抱在怀里,坚持要把事情做完再走。大家各执一词,任谁也说服不了谁,山下的人声开始鼓噪起来,惹得众人心烦意乱。谢源将火把戳在泥地上熄灭了火焰,李紫官以为他是在逼自己就范,绝了火烧的念想。从自己衣服里取出一盒火柴,冲他嚷道:“你这个白痴!我自己来!”
“你说什么呢!我是怕下面的人看到这里有火光,”谢源一拳砸在自己的掌心上,眼睛涨得鼓鼓的,和自己在学校高谈阔论时一样,他喜欢那种振振有词的演讲家风范,他转而对大家说话,“现在是争执的时候吗!我们若是在这里被他们人赃俱获的逮住,还革什么命!暂时的困难不能左右大局,我们这次行动实际上已经得到效果,为什么不保存实力为今后作打算?”
“过了年还要开学……”
学生们都为这句实在话附和起来。李紫官看其余人去意已决,咬着牙关嫌恶地笑。
“我们分头走,”谢源对大伙说。他看了看半响没发话的我,又去看李紫官,改换成柔声向她说:“紫官,你走不走?”
“你们走罢,我留下。”
谢源的面孔变得一阵铁青,不再留恋地转头带领着众人往山上走,走了没两步,他回头看我还站在原地。吃惊又嫉妒地说:“你也要留下?”
我没有答话。实际上此刻我的心头也是五味杂陈,恨不能赶紧脱身,远离这场滑稽的噩梦,但身边的李紫官又像是某种巨大的能量在诱惑着我,我悄悄看着她决绝的摸样,用力攥了攥拳。
“李元孝,别说不给你机会。”谢源扔下这句刺耳的话,走了,其实他这醋劲倒是鼓励了我。至少,这次的革命,主动在我,结果是什么呢?只留下我和李紫官了,我和李紫官站在一道,胜利在我。
谢源和其余人等的身影很快隐没在山林里。空留下我和李紫官两个人,偌大的木料场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幽深和庞杂,这时候我才确实感到初春的寒意,树丛间吹来的风,酥麻蚀骨,我定了定神。再看李紫官也在瑟瑟发抖。
已经有几个搜山的人率先找到这里,我和李紫官悄悄躲在外面堆放的木料后面。他们几个人四下找了找,又去了别的地方,但不久,后面巡山的人也陆续跟了上来。我们等着几波人过去。李紫官靠着我,我拨开她跳到我鼻子前面的几缕头发。
“然后我们怎么办?”
李紫官用气音说:“进去里面,货仓里面总不见得这般潮湿,我们到里面点火,快。”
我们刚一起身,就听到十步远的地方有人声传过来,“那边是谁!”
接着一个人声说:“谁呀?”
我们赶紧把头压低,听到另一个声音说“抓住把他们钉在城楼上。”一时之间,我以为四面八方都是人的说话声。
“你也就嘴巴厉害……”他们说话的声音渐远,但嘻嘻嘻的讪笑声却在我脑际引起了难言的恐惧。我不敢抬头,旁边的李紫官却似乎在这场面里出奇的镇定,依然毫无退意。
等他们走远,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埋头跑到最靠里的那间货仓,这里暂时还没人查看。
门用链条拴的大锁给锁上了,钥匙倒是大方的挂在墙上,淋了雨,我拿过来,赶紧在衣服上抹了抹。这时候东边的林子里也有人上来,四处的出路就要断绝,此时就算货仓里真的有条件生火,进去里面也是自绝退路。
我已然想不到本来的使命,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面朽木的门前,像是一个被自己惊吓过无数次的狼狈的猎物被人追逐?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要把李紫官送进这间货仓,这是我此时此地唯一的欲求。别无其他。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但锈蚀的锁孔如何用力都无法扳动,换手也使不上力。此刻我脑中一片混沌,一边是李紫官在催促我开门,一边耳畔又不绝响起乡民们靠近的吆喝声。而越是心急,钥匙在手里就越是听不得使唤。
“罢了罢了!元孝你也走吧!”
“打得开!李紫官,我成的!”我的脸不知变成了什么可怖的摸样,李紫官看着我的脸,竟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用手捂住嘴,头发打蔫似的贴在脸上。
我顾不得别的,回头继续和钥匙咬住劲。
终于,乡民们兴师问罪的声音压过了李紫官。亦或是我胆小产生的错觉。我失了心智,钥匙卡在锁孔里进退不得,再一用力,锁孔发出咔的一声,我喜形于色,不料这时候气运已尽,拧动的瞬间,锈蚀的钥匙不堪重负,掰断在锁孔里,只余下一小节露在锁孔外。我喘着粗气,两眼紧盯着断在锁孔里的钥匙,难以置信这难堪的境遇,突然发狂般的用双手推门,也不过是换来门扇不住的晃动,使得粗重的链条摔在门板上,砸出心跳那样节奏的阵阵闷响。我放弃了挣扎,双手撑在门板上,长呼出一口气,最后两手猛地拍去门板,不巧撞在锁具上的棱角,右手掌心顿时鲜血淋漓,李紫官也吓得怔住。我却感不到丝毫疼痛,只觉得无限的羞愤和屈辱。不一会儿,手上的鲜血又洒在地上,钥匙把也浸湿了。我直挺挺地甩过身子,近乎是闭着眼,头也不回的跑开了,一直跑,跑进了夜晚的树林里。
我没有听到李紫官发出什么声音。或者是,她一直在叫我,我却假装听不见?
总之,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紫官,我们之后还常常见面,她也未必见得为这桩事记恨我,甚至,我感到她开始在同情我,对比从前,她待我还要更加友好了,只是她的“革命行动”,再也没有找我参与过。这最叫我无法忍受。她每次出现,或是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她,都无法逾越除夕那晚的事情。
我把李紫官一个人丢给了乡民,她是宗家的大小姐,人们总不至于对她过火。想到此,我为自己准备这样的借口感到羞愤。
那件事实际也没有波及到我,因为率先被逮到的小野等人,并不知道我中途被李紫官拉入了计划,后来“归案”的谢源等人,也意外的没有将我供出来。我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安全而可鄙的被他们英雄般的排斥在外。县里一时为学生的堕落感到惊惧,好笑的是,一开始在北城门抓住小野等人,还不知道他们在偷盗什么,事后知道是城头上的旗子,不免虚惊一场,忙于搜山的樵夫们以为真的有革命党在闹事,后来知晓他们对付的是本县的几个年轻“秀才”,更觉得大失所望。事情终归没有闹大,各家关起门来象征性的对学生们进行了责罚。这样的恶作剧,很快就被新事掩过了。
而我,只有我停留在那个晚上,默默地活在痛苦的愁闷里。直到李紫官被她父亲逼迫退了学,一个人离开了樵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