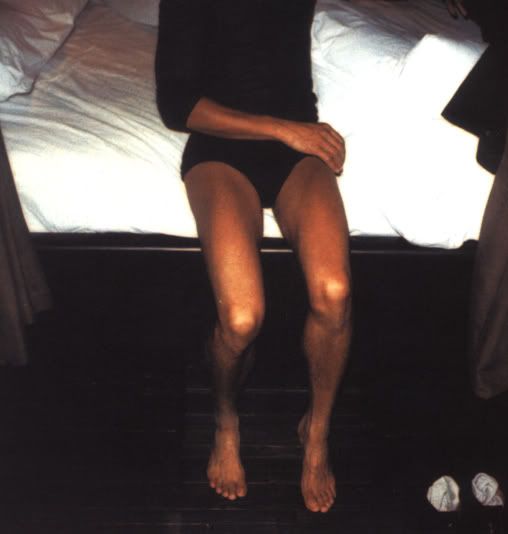- 最后登录
- 2010-1-3
- 在线时间
- 0 小时
- 威望
- 0 点
- 金钱
- 458 点
- 注册时间
- 2007-8-4
- 阅读权限
- 20
- 帖子
- 403
- 精华
- 0
- 积分
- 787
- UID
- 1509

|
邱志杰
在中国,在省会或省级直辖市所出现的当代艺术形态,其直接基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是发生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的辐射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欧美模式的思路。其原型是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相反,当代艺术运动发生之前的近50年的社会主义艺术和文化生产机制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比起北京和上海要来得更明显。中国的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因为有其政治宣传诉求,以及新中国文艺思想中的民间取向,始终注重艺术知识的普及重于提高。遍及全国各地的群艺馆和文化馆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与美国完全依靠基金会来捐助图书馆,美术馆事业,导致这些事业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模式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通过群艺馆系统,民间艺术得到整理,传统艺术得到普及。即便是在一些没有国家级的名家指导的地方,年青人也有机会获得比起北京和上海的同龄人相差无几的艺术教育。
他们感受到同样的时代氛围,也有着相似的知识准备。比起大城市的青年,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语言可能不够圆熟,但他们的综合文化教养却往往更好。中型城市的特点之一便是各种文化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比起大城市来得更频繁,地方不够大,使各种行业的精英人物之间很快建立起“名流”之间的私人交情。只要一个城市达到有一间师范学院级别的大学,就会存在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从而为文学,艺术和音乐领域的互通制造出一种氛围。而中型城市更便宜的物价和更传统的人际关系,使制作作品的绝对成本比起大城市要来的低廉。这就是说,他们的艺术生产能力是足够的。真正的差别其实是在于他们被观看和观看别人的的机会较少,他们远离有影响的全国性的媒体。
因此,在当代艺术处于疯狂生产的时期,地方上的艺术家比起艺术中心的艺术家毫不示弱,甚至更凶猛一些。在80年代中期“新潮美术”兴起的时候,地方上的艺术家的作为超过了北京上海。如黄永平在厦门组织“厦门达达”的运动,第一次展览就是在厦门市群艺馆展出的,这是因为运动的成员之一靳乃进本人就是群艺馆的工作人员。(今天活跃的中国艺术家,谁没有一个来自群艺馆、文化馆、少年宫、中学或地方美术家协会的启蒙老师?)--“厦门达达”的第二次展览就是在福建美术馆举办并被查封的,这在今天都不容易想象。在在浙江省的舟山市也是,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吴山专和倪海峰,当时都是群艺馆的工作人员。在四川,四川美院的画家们和地方批评家紧密合作,也创出了独具力量的绘画流派。
只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观看”才变得和“行动”一样重要,获得信息和传出信息,不但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后续工作,也被看作是艺术工作本身的一个合理部分。就国际而言,中国需要被西方观看;就中国国内而言,云南和湖南需要被北京所观看,并获得来自北京的信息。地方上的方便的创作条件和来自各领域的几个知交好友,足于互相取暖以维持创作激情,却不足于进一步带来成就感和事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了外地艺术家旅居北京的现象,在九十年代末,上海的经济成长时期也成为一种选择。
朱发东可以以同样的价格在昆明得到大一点的工作时,却愿意在北京菜市口的一间小平房里蜗居,对他来说,被看到的过程就是一种工作,后来这一点果真成为他主要的创作话题。出于同样的理由,马六明从武汉来到北京东村,变成“芬·马六明”,其主要议题也是“观看”。长春的黄岩,一直以家乡为基地搞他的“邮寄艺术”—---以向各地的朋友邮寄明信片的方式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名声。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移居北京。
这样的变局促使坚持在地方上搞艺术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如果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可能移居北京,就会组成艺术小组性质的集合体,以团队的方式一次次的组织进京展,对北京的观看发起进攻。如湖北的“新历史主义小组”所作的那样。
这样的“冲出XX,走向XX”的模式的无意义,在中国艺术这么多年的国际闯荡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照见。旅居北京的各地艺术家有些人成功了,成功的结果是汇入了北京的文化生活-----就向旅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最终结果是汇入当地的文化生活一样,黄永平代表法国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是一个最显眼的信号。他们的成就足于鼓励家乡的青年的地方自豪感,但更多的时候只会成为谈资,他们所来自的地方并无多大收益。而群体的“冲击”比个人奋斗更难于奏效,因为它难于被中心城市的掌门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来加以利用,他更难以被编织进北京或纽约的叙述。而群体自己本身很容易陷入权力之争,在大家一起来到中心之后,在个别人率先得到一些好处之后,群体就会空前脆弱,迅速瓦解。事实上,一次比较成功的进京展往往就是一个地方群体解体的谢幕礼。
走出去不行,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便选择了请进来。福州在九十年代末接连三、四年每年举办全国性的“当代艺术邀请展”,花了不少钱,福州本地的艺术家大忙特忙了一场之后发现,除了交到一些“名家”成为私人朋友之外,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没有任何提高,城市本省的地位只有小范围的提高。这个教训值得总结。原因很复杂,一是因为这些当地的艺术家注重活动得热闹本身,而没有意识到作品质量才是最更本的。他们古道热肠地请人来“交流”和旅游,而忘了自己和名家们还是存在着竞争的战斗关系的。对于“名家”们,你只能把他们比下去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把他们打服,不可能通过买单让他们说你的好话。---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他们尽会好话连篇,但在真正严肃的场合他们绝对会表现自己的苛刻的眼力的。其次是因为这些活动以实践性的一次性消费居多,即是福州这样富庶的城市有能力连续的高,也只不过是连续的事件,并没有在本地成功地启动正常的常规性活动的机制。热闹过后,一切依然故我。黄岩在长春也搞过两次这样的事情,一次是以录像展的名义,一次是很名不副实的“网络艺术”展,就是因为着眼点在于事件而不是当地的制度,最后他自己还是来到了北京。------这一顿比照,希望对湖南的朋友们有一些用,但其实我的真正的谈论对象是我们的北京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我们在邀请国际大腕的时候要多想一想福州的遭遇。
真正对当地的艺术活动较有建设意义的是地方媒体的力量,在纸上印刷的时代,即便是一个编辑部处在中型城市的媒体,通过全国的发行网络,也有机会成为全国性的学术平台。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当然是南京的《江苏画刊》,正因为江苏画刊是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南京一带的艺术家的潜在地受惠,并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广州“大尾象”小组的影响也和广州的《画廊》杂志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力量有关。同样,湖南的艺术家们最风光的时候也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最活跃的时候。
到九十年代末,随着上述纸上印刷媒体的衰弱,艺术活动最大量地集中在了有限的几个中心城市。然而,相应的又产生了新的变局。
第一个现象就是网络媒体的兴起让地方精英建立自己的游戏方式发生了可能。网络改变了人际交往形态,消解了距离远近带来的优劣力量对比。在网络上频繁联系的两个人会比同住一座城市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有着跟近的交际。有影响的沪两旺媒体,比起过去杂志对信息的需求量要打得多。以前的杂志成本更高并且容量有限,对发表的内容也就更有选择性。而网站低廉的成本和和几乎无限的“吃进”信息的能力,使善于频繁造事而处在“边远地区”的艺术家和艺术家群体的位置向“观看”的中心移动。比如,拥有强大的写作能力和记者素质的艺术家岳路平的作用,使西安所发生的当代艺术事件在“美术同盟”网站上的“见报率”远远高于住在通县的艺术家们,尽管“美术同盟”的主编就住在通县。互联网的发展,使地方性的当地艺术实践的“天时”。
第二个重要的现象是“独立艺术空间” 成为地方性的当代艺术活动的主要平台。中型城市建立独立艺术空间的条件比起北京有自身的优势,尽管北京建一个就会被“看见”一个。其最成功的例子是昆明的上河创库艺术空间群,其低廉的租金使它免除了北京的同类艺术空间的焦心,并有机会成为当地的时尚中心,引起地方媒体的追捧。在艺术空间存在的前提下,旅游文化资源只要应用的当反而可以转化成为话语权利。所以不但创库崛起,丽江和大理也跟着崛起,在云南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艺术生态链条。在南京,圣划艺术中心的成功运作不但帮助了南京本地的艺术氛围的成长,起到当年江苏画刊所起到的作用。也成为沈其斌和金锋进入上海的话语圈子的本钱。在这个意义上,沈、金进入上海,与当年的地方军的进京展是绝然不同的。
在北京和上海,独立艺术空间本身已经产生一些问题,他已经到了面临转型的关头。但在地方城市,依然是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模式。这是我向西安和长沙这样的地方的朋友们的建议。昆明,南京的成功经验大可借鉴。要精心地设计自己所在的地方的“地利”。
当然,一个地方文化生态的建设,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没有叶永清这样的人,就没有云南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毛主席说的:决定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毛主席家乡的艺术家们对这个应该有深刻的理解。
依照话语的惯性,我下面将要表述地方性的当代艺术实践的“人和”要素。这样的要素的出现还是和“观看”有关,站在西方的中国艺术观察家们们不可能永远那么粗疏的把中国当作铁板一块来表述。这样的整体性表述当然大体是准确的,但也难免是经不起细细追究的。更深的研究就会发现地方性差异,从而成为一个研究者否定前面的人的结论的最有力的证据。他们之间的知识/权利竞赛会自然地迫使他们这样做。我干在这里预言,很快地在汉学界,研究四川或者湖南的当代艺术的专家,就会比一个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专家显得更像一个专家了。
这时候,最敏锐的那些“观看”的活动的提供者们很快嗅到了这意思。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广东快车”就是一个例子。最近在挪威国立当代艺术馆展出的《上海拼图》这个展览又是一个例子。很快就会形成一种有一些庸俗的,但对西方人却是确实有效的“进步话语”。那就是,北京,被描述为受到中国政府的不明智的意识形态压抑的地方,于是在那些地方的艺术过渡地陷入对抗的怪圈,最终沦为使馆艺术。而像上海,广东这样的地方由于经济成长,才真正出现了中国的新的艺术。这样一种论辩潜在的意识形态逻辑是:自由和人权是好的艺术出现的必要条件,这是西方所乐于看到的。
他的艺术社会学逻辑,则是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文化繁荣这样一种经典的、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中影响极深的社会决定论话语。因此很多中国人听起来也可能会觉得有道理。
而这种论辩的最可能的流行病灶,是西方所传播的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导致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前提下,上海的摩天大楼被想象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摩天大楼下的下岗工人,和建造摩天大楼的外来民工,他们所象征的紧张的社会冲突,则被想象为中国威胁的原因。
这样一种叙事显然是潜带着一种欲望的,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北京渐渐的在话语中成为一个不可见的中心。而发生在上海的任何一件小事,出现在广东的每一个在不成熟的艺术家,都会得到机会被反复地讲述、放大。即便同类的事情在北京可能多的不可胜数。这种话语中有其泡沫因素,就像整个“中国热”本身一样----中国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也都会被放大,尽管同样的事情很可能在纽约其实也不很稀罕。但是这种泡沫也会有其可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要看到他的泡沫性。
现在风头正健的广东和上海话语的策略,是把他们与北京的差异,由一种空间关系描述为一种时间关系,一种进化。这样一种话语的危险在于它的推论:他打不倒北京,却会使长沙,西安,昆明和重庆,成都的艺术家们找到一个口实。既然可以用南方的优势来否定北方,也就有机会用西部的优势来把整个沿海都指责为殖民主义的后果。西部并不缺这样的能言善辩之人。而且,这也会是更下一拨的汉学家会期待发生的。这也正是长沙这样的地方的艺术家要警惕着着去加以利用的“天时”、“地利”、“人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