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登录
- 2019-8-30
- 在线时间
- 8260 小时
- 威望
- 7223 点
- 金钱
- 29678 点
- 注册时间
- 2007-8-4
- 阅读权限
- 70
- 帖子
- 7872
- 精华
- 10
- 积分
- 10282
- UID
- 279
  
|
刚刚在台湾出版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
十二月的斯德哥尔摩阳光稍纵即逝,这一天却天气极好。早上十点,红线地铁终点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镜。头戴礼帽的马悦然和他的妻子陈文芬如约出现了,开车带记者和摄影师去他们家中。
一辆略显陈旧的灰蓝色沃尔沃小轿车,87岁的马悦然开起来仍然得心应手,他熟练地加油门,打方向盘,转弯。车子穿行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林野公路间,两旁的景物渐渐有了一些美式景致,低矮而舒适的房屋,间杂在绿树与深蓝色的波罗的海之间。“这片住宅区原来是艺术家的聚居区,后来富人多了起来,变成著名的住宅区。”
但马悦然并没有在这里拥有房产,而是长期租住在一座养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据陈文芬说这里非常受欢迎,很多人排长队申请,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轮上。马悦然自1998年起住在这里,中间也搬过三次家,才换到现在居于二楼风景更好的房间。而楼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师。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绿树红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斓。马悦然夫妇一路带着我们介绍这是山毛榉,那是古橡树,走向波罗的海边还有瑞典独有的柳树,以及大片的芦苇。事实上,除了亲近自然,马悦然夫妇并没有过多参加社区活动,只是偶尔打打桥牌。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斋里奋笔疾书。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房一厅不过70平方米左右。一个10来平方米的客厅完全成为工作室,正中摆着一个大长条方桌,上面铺满各种书籍、记事本和马悦然的戴尔电脑。而陈文芬则在房间一角有一张小方桌,没有座椅,她说坐地上工作对腰椎更好一些。
房间里有各个出版社、作家寄来样书、著作、书信、纪念品,书法等等。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个小宇宙,它所发出的电波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因为书斋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对于马悦然,中国作家群可谓又爱又恨。这样一位能读懂他们作品的外国老头,在过去26年来一直作为至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懂中文的评委。在广泛的想象里,他的态度和爱好是中国作家能不能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于是有人乐于与他结交,也有人公开表示不喜欢他。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投射到马悦然身上,成了一个古怪的混合体,他们希望马悦然通读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后做出一个“客观”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种酸涩的心理,对中国作家的“命匙”掌握在这样一个外国汉学家手里表示不屑和难以接受。今年以来,一连串的风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陈文芬会为马悦然打抱不平:“希望悦然读完所有人的书,那是图书馆员的工作。悦然和普通人一样,只读和翻译他自己喜欢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马悦然依旧保持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译着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认为译者是“作者的奴隶”,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欢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奴隶。
就像这个冬天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财产,去还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债务了。”而马悦然显然很乐意做老朋友的“奴隶”,他在2004年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刚刚在台湾正式出版。
我们的采访话题,也就从特朗斯特罗姆得奖开始。
B=外滩画报
M=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罗姆的友谊
B:今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得奖了,您以前说过他是早应该得奖的,这次您是不是很高兴?
M: 非常开心,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记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获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时候,刚好是托马斯第一次访问中国,你们一起在北京,对吧?
M:对,那是1985年。当时我在北大有一个演讲,当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罗姆那时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讲。
B:还记得在北京和托马斯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吗?
M:我获选院士当晚,瑞典驻中国大使请我们吃饭。饭后又继续到大使家喝酒。大使问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种绿颜色的蛇浸泡的,看起来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马斯都喝了。后来托马斯到了上海,写了一首诗《上海的街》,还写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涩,回味不止。”
B:托马斯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M:他很欣赏中国。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会不自在。有一天他说我们找一个人少安静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馆借了一辆车,带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时常去的安静之地。结果开车去了之后,却看到至少八辆旅游大巴,带了很多游客去,根本就走不动。
还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朗诵结束,有一名男生举手说他听不懂。托马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这诗当作是自己写的。我可以送给你。”
B:您和托马斯是怎么认识的?
M:我们大约是1966年在诗歌朗诵会上认识的。我们后来也经常聚会,有时到他家,有时到他在龙马屋海岛的蓝房子去,那是他当海员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后来中风了,您有什么反应?
M: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位好朋友告诉我托马斯中风了,我非常难过。如果没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马斯现在一般只能说四句话: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没办法和托马斯对话。如果莫妮卡在,无论你问托马斯什么,莫妮卡就看托马斯的脸,就能回答了。然后托马斯再表示对还是不对。
有一天,我在他们家里,托马斯突然用笔画了一个马头,交给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马斯又再画了一个马头。莫妮卡说,哦,你要找一副眼镜。我就问,托马斯要找副眼镜,他为什么不直接画一副眼镜呢?莫妮卡说,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人。马头和眼镜的关系呢?原来,在托马斯一首叫《打开的窗子》的诗里有最后几句:“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B:您是如何开始翻译托马斯的诗集的?
M:1983年过年的时候,我住院开刀。当时托马斯刚出版了一本诗集,叫《狂暴的广场》。我早晨两点就醒来了,我就开始翻译他的诗集,当天下午六点就翻完了。那时我打了麻醉药,脑袋里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译这些诗,把它们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绍北岛翻译他的诗集。后来我还翻译了他一本散文诗叫《蓝房子》。
2004年在台湾时候,碰上“总统大选”的“诈弹”闹剧,我和文芬就到乡下避住。把托马斯最新的两部诗集《巨大的谜语》和《悲伤的凤尾船》翻译成中文,后来应陈思和的约稿,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但没有出版成册。今年托马斯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台湾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马斯作为近40年来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国内有什么反应?
M:大家都觉得实至名归。这和上次1974年埃温德.雍逊 (Eyvibnd johnson)和 哈瑞.马丁松( Harry Martlnson)这两位瑞典文学家得奖时遭到非议相差很大。那次获奖,因为他们和瑞典学院有一些关系,在瑞典国内引起很大争议。最后哈瑞.马丁松还自杀了。托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个文学奖,对于一个900万人口的国家是有点多了。但如果不颁发给托马斯,我们就更不能颁发给其他诗人了。而上一次得奖的诗人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距现在已经有15年了。
B:得奖后您祝贺了托马斯吗?
M:当然,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了。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和莫妮卡通话。我太太陈文芬也参加了在瑞典学院举行的托马斯作品朗诵会,她用中文朗诵一首托马斯的诗。
“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B:您刚才谈到了15年来第一位诗人得奖,是不是因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对诗有一种呼唤?
M:你没提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不过确实是的,这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大家都觉得今年应该颁奖给一位诗人。诗歌确实是对现实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
B:您对诗歌是不是有偏爱?
M:在中国文学上,诗歌所占的成分是很重的。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报国寺,开始学中国文学。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很多汉朝乐府和南北朝诗,也读了《唐诗三百首》。不过我太不喜欢《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这种选本,这种选本是很危险的。一个人读完了《唐诗三百首》就觉得他读完了所有唐诗,读完《古文观止》就觉得读完了中国古文。而这其实只是几个编辑的选择眼光。
B:这么多朝代的诗歌,您对哪个朝代的诗歌最有偏爱?
M:我教书的时候,就问过学生,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们愿意生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如果我来选,我就选择生在南宋,那是辛弃疾的时代。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词人,苏轼、陆游好,但还是辛弃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进词牌里,却又很自然。
B:很多人觉得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很像唐诗,比如王维,您怎么看?
M:我觉得不太像。他的诗不是田园诗,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国当代诗人的交往是怎么开始的?
M:1981年我就请北岛和顾城进行诗歌朗诵。北岛根本不会朗诵,他只是“么么”地张开嘴巴。而顾城是会走路的诗,是长着两条腿的诗,他朗诵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后,1983年我就把他们的诗翻译出版了。结果很受欢迎。
B: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
M:艾青和闻一多。
B:艾青和闻一多,与北岛和顾城,其实是两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后者是您晚辈。您在翻译的时候是如何进入这两代人的心境和时代背景?
M:他们确实是不同的两代人。你要读了又读,读到听懂了他们的声音为止。我和北岛谈过中国诗歌的历史,我发现他和顾城、杨炼等对五四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了解不够的。我和他们谈过闻一多和徐志摩,他们都基本没有读过。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岛在我家里,我拿出自己喜欢的1920年代的诗歌,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问他读了怎么样,他说翻了一下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卞之琳就比北岛朦胧一万倍了。而北岛可能觉得“朦胧诗”是他们创造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但也要看到中国诗歌历史的传承。
B:您在翻译北岛顾城之前,已经有很多年没到中国,如何体会中国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
M:虽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国,但我仍然对中国的情况发展很了解,所以这方面没有问题。
B:您当时接触的中国诗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命运各不相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各自的变化发展?
M:过去有流亡诗人这个概念,现在流亡没有意义了。很多人都回归中国了。北岛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安顿下来了。中国作家的生活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几个地方都有房子。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欧洲相比这很不错了。
B:像您现在还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里,和他们相比觉得怎么样?
M:我这个人对钱有点不耐烦。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太太陈文芬补充:中国人的财务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欧洲国家福利比较好,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他当年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 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他翻译一本书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够用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的老师高本汉,他是伟大的汉学家,但他去世的时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读书而已。
B:我刚才的问题其实是,三十年来中国诗人主要有两种发展轨迹,一种是国际行走,一种是扎根本土。您觉得对中国诗人来说,是通过国际行走以求与国际接轨,还是扎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可呢?
M:东德的作者,在柏林墙倒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有一个对抗的对象,政治变了之后有一个失落感。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比过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表达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赏的是文学的价值,像曹乃谦的作品翻译到瑞典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只要译者能够读懂,并把它忠实地翻译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
B:对于汉学家这个角色,有一些中国作家会有异议。您觉得汉学家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M:一般中国学者认为,汉学家就是外国人。因为没有中国的汉学家之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差别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师高本汉,那时他的学术范围是非常宽的,而现在的汉学家则越来越窄,只是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了。
B: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M:现在的汉学家对上古历史,对汉语音韵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真正的先秦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几年,孔子学院对西方的汉学影响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学院合作,大学里的管预算的决策者会说,中文系既然已经有孔子学院就够了。但孔子学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话了,和汉学和研究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原来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变成教汉语的学校了。
B:您对您的弟子这一脉还有要求吗?
M:我对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这确实有大环境的影响,我对瑞典汉学的发展有些悲观。原来瑞典的远东图书馆是欧洲最好的汉学图书馆,但现在基本等于关门了。原来的图书馆员遣散了,现在图书馆只供参观,图书馆员也不懂中文,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觉得汉学家是中国文学的评判者,您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M:我觉得不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的国学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贡献,像我的老师高本汉一直做音韵学的研究,里面有很多方面中国学者也还没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的参考。
B:因为您处在诺贝尔奖终身评委,而且是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没有感觉到中国作家对您又爱又恨的感觉?
M:我想起一个事,杨牧的作品被介绍到德国的顾彬那里,顾彬说要让杨牧把作品给他翻译,他就能帮助杨牧在德国出名。但我看了顾彬的翻译,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译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隶,完全忠于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删改或者随意演绎原作的内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译者,而不是一个桥梁或者推手?
M:对,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当人家的奴隶。
B:您最近有没有发掘一些新的作家,准备翻译他们的作品?
M:最近曹乃谦出了一本新书,叫《佛的孤独》,我翻译了之后在帮他进行一些推介。残雪也很好,她是中国的卡夫卡。我的一个学生在翻译她的作品。我还准备翻译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进行翻译?
M:每周公务还很多,瑞典学院还会固定开会。夏天的时间会多一些,整个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们会到乡下住,那时翻译的进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没有翻译中文作品的计划?
M:最近翻译完台湾诗人痖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还翻译了台湾作家杨牧的120首诗。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之后,看看要不要继续我2008年翻译出版的《道德经》再翻《庄子》。
B:您已经年近90,接下来几年里还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高。我有个小本子,做翻译的时候每天记下自己的工作计划,基本都能按计划完成。我原来有个愿望,是想翻译《左传》,它是先秦文学最伟大的著作。《左传》和《庄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么喜欢辛弃疾,会翻译他的诗词吗?
M:我翻译过他《沁园春》词牌的十三首词。以后还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还会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写的微型小说,出版社起名叫“笔记体”小说。我写了60篇,文芬写了40篇。书名叫《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游,幻想辛弃疾和李清照来和我喝酒等。这是受莫言写的《小说九段》的启发,但我写得比他更短。
B:有没有想写回忆录呢?
M:瑞典文已经写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讲了我在1949年在中国的经历,听众都很感兴趣。中文我出过《另一种乡愁》,也讲了那一段经历,但还不算传统的回忆录。我可能会继续写。来源:外滩画报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加入黑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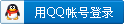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