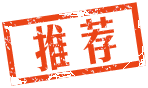- 最后登录
- 2014-3-6
- 在线时间
- 292 小时
- 威望
- 1415 点
- 金钱
- 0 点
- 注册时间
- 2012-5-12
- 阅读权限
- 0
- 帖子
- 46
- 精华
- 0
- 积分
- 0
- UID
- 50590
 
|
这件恶心的事情发生在去年的夏天,他用沾有肉汤的馒头将一只流浪狗引进了一条一头封死的巷子,那条狗骨瘦嶙峋、整条脊梁如尖刺般清晰可见,那样子就像才搭好表皮没来得及塞填充物就上场的傀儡,肚皮紧紧贴住骨头。它瘸了一条腿,只能一跳一跳地跟紧它的食物,舌头不住晃动。它饿得发昏,全然不顾后果,肉汤的香味令这只可怜的生物丧失了理智,而他的前方,那个一脸和善却令我毛骨悚然的家伙手正手捏着馒头,一步步朝后退着,要不是它残了一条腿,我想他定会遭殃,他会被这只饿昏了头的流浪狗咬断手指,搅着馒头一块吞进肚里。他退至巷口,停住脚步,那条狗也跟了上来。突然,他一转身,将手中的馒头抛了出去,馒头在空中划出弧度,顿了数秒,接着,掉落在巷内,翻滚,直至停住。那只狗就像是疯了似地冲进了巷子,有那么一会儿,我觉着它的腿没瘸,它不过是个骗子,一个博取同情、老道的骗子,但等它一口吞下最后那块馒头,转回身时,李已从地上抓起了那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棍,冲着它走了上来。这时,它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这一切绝不因怜悯,而是一个疯子设下的死亡陷阱,它才稍稍填好肚子,还来不及恢复一丁点儿体力,就得命丧黄泉。我不知道这可怜家伙的腿是怎么断的,但它在挨了一记铁棍“嗷嗷”乱叫的样子却令我整个心都揪了起来,我差点没尖叫,而接下来的场面,让我连隔夜饭都呕了出来。那只狗在挨了一记闷棍后,往后退了几步,它的整个身子都抖动了起来,声音开始变得低沉。它身体晃动,迅速后退,躲开了接下来的攻击。这时,它忽然顿了下来,全身的重量都往下压去,那条断腿往后猛地一抽,跳起来想要咬住李的手,但,被李迅速躲开。它被一脚踹在了脖子上,整个儿扭动着飞了出去,撞在水泥地面上,滚了好几米远,脑袋折了过来,腿不住抽搐。我以为李会直接冲上去要了它的命,但他没有,那条狗也迅速站了起来,只是身体仍不住地摇晃。它的头低了下去,露出满嘴尖牙,发出低沉而又敏感、愤怒的叫声。它试着调换一个角度,但那条断了的后腿却不怎么听使唤,差点没再摔倒,如果那样,它就该完了。我想它知道自己的处境,那是动物在濒临死亡恐惧时才会显现出来的力量,它们会奋起一搏,压上最后的赌注,只是对于它那依旧空空如也的肚皮、如尖刺一般的肋骨而言,似乎太晚了。它使出了最后的气力,如弹簧般一跃而起,我看见它的那条断腿狠狠地撞在了地上,接着,李抬起来的那条准备如法炮制回踢的腿被一口咬住,但它立即就被顺势给踢了出去,这次直接撞到了封路的那道墙上,发出一声闷响,像是用铁锤砸断一根干硬的骨头以及骨骼摩擦而至的“咯咯”声。李的小腿被血染红了一片,他握紧手中的铁棍戳了戳被咬伤的部位,像只被彻底惹恼了的猫那样尖声笑了起来,转而冷哼,听得我头皮发麻。他将铁棍扔在了地上,伸手从腰部的皮带上抽出那根将近两尺的铁钉——那东西被他别在皮带上,在他白色的T恤上戳出了一个洞。那只狗拼命地叫着、扭动着、抽搐着,使劲地咬着地面,发出“咔嚓、咔嚓”的摩擦声,身体弓起又伸直,四肢拍打着地面,不停转动,眼神里满是愤怒,然而绝望的神情却充斥着整具瘦弱而又渺小的身躯。它不住地抽动着,但已经站不起来了,等待它的将只有死亡,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愤怒以及可怜巴巴的恐惧。
那哀号声令我连心脏都几乎跳停,令我至今难忘,我亲眼看见那根铁钉穿过它的头颅,从一边的眼眶插了进去,刺穿了头骨,从另一面透了出来。它的头部被涌出的鲜血染成了黑色,混合着晶状体以及脑浆,一直流进了牙缝。那家伙丝毫没有将铁钉拔出来的意思,他握紧一端,用力将另一端透过那可怜生物的头骨插在地上,这样,那条狗的整个头都贴紧了地面。它的身体疯狂扭动,脖子扭转过来折叠在了一起,肚皮翻开,四肢朝上,全身抽搐。他站了起来,一脚踩在它的脖子上,它的身体猛地一缩,撞在了李的另一条腿上,接着,传出一阵“咔嚓”的响声,而这时它的叫声已不像是由喉咙发出,更像是某个极远角落传来的微弱不幸求救声,但我想,它恐怕连哀叫的气力也快要竭尽了。我看见它的身体反复扭打撞击在李的一条腿上,而头被另一只脚用力踩住,那根铁钉就仿佛是一杆标旗一般竖立在那个眼珠迸裂几乎就要掉出来的眼眶里。它的脑部受损,失去了主观意识,只本能地扭来扭去。它的那条断腿此时又已重新折开,嘴边的血伴着唾液沾上地面的灰尘染红了一片,头部黑色的液体黏稠得仿佛凝固了一般,而下颌在遭受了一系列撞击后已经变形,几乎是冲着上腭斜插而去,这时,除了那条断腿仍在抽动,它的整个身躯变得一片死寂,如同一条掉进沸水的小鱼般无声无息,随着沸水上下翻动,连可怜巴巴的痛苦也叫沸腾声给淹没了。
他猛地将铁钉拔了出来,几滴参杂鲜血的白色液体掉落在地上。它的脑袋被迅速提起又撞回到地面,一股液体如挤压般从那个黑洞洞的窟窿里流了出来。它的脖子早就断了,一颗眼珠串在铁钉上被李舞动着挥来挥去,双嘴紧闭,舌头从中断裂,一截留在了嘴里,另一截落在了它的耳朵旁,叫灰尘裹着分不清颜色。它的四肢摊开,原本不住挥动的尾巴瘫软缩成一团,一股浑浊的液体将下身浸湿,灰尘打在上边,毛发一簇簇卷缩起来。李朝它狠狠地踢了几脚,发现它全然没了动静,就蹲下来,握紧铁钉刮擦着水泥地面将那颗眼珠刮了下来,发出令人恶心的“嚓嚓”声。他似乎是厌倦了,又站了起来,转过身来看着站在巷口的我。
“把刀拿给我。”他的手指冲向巷口,那感觉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不过是碰巧路过,一切平静,而我整个人都已经傻了,只知道机械性地转头、低头。我的脑子那一刻空空如也,一只手顺着胸口伸出一把勒住我的脖子,令我喘不过起来。我感到整个巷子都在绕着我转动,那一刻,我觉着自己快要死了,那个男人,那个令我毛骨悚然的男人,会在下一分钟,就如同对付那条流浪狗一般将我弄死,那根铁钉会穿透我的头颅,我的脖子会被扭断,骨架如多米诺骨牌那样倒落殆尽,而我将连一点求救声也发不出来。
我盯着他手中的那根铁钉,前一分钟才从那可怜生物的脑袋里拔出,上边还沾着血,血还没有凝固,下一分钟,就会插进我的脑子,透过头骨。那绝不会比摔一跤来得好受,我的脑子将“嗡嗡”直响,整个世界都会是金属摩擦骨骼的响声,碎骨会和脑浆搅动在一起,而前一分钟,我还在目睹一场才平息的杀戮,那已经是一具尸体,灵魂已遭扼杀,鲜活的生命也已湮灭。
他会杀了你,我的脑子里反复地响着这句话,你不该目睹他的凶残,你的下场,绝不会比那条狗来得安宁。
“刀在那里。”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又用手指了指巷口。我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好吧,是你多虑了,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这却令我更为紧张。
那把刀藏在垃圾桶侧面,长度超过一尺,上边满是锈迹,但刀刃锋利,显然是才经过打磨,也许是匆忙,也许是他并不在意这外表,但我觉得那片锈迹却更像是鲜血干涸凝结而致,留下来,不过是他那残忍秉性的又一扭曲。我抓起那把刀,刀很沉,刀背宽而结实。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他正用脚将那颗破碎的眼珠一脚踢开,嘴里说着我听不清的话,我知道,那是诸如“狗娘养的”一类的脏字。也许我该将这把刀扔过去,扎进他脑袋,我想,我该狠狠地掷过去,对准他那张狰狞可怖的丑脸。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这想法吓我一跳,我觉着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了。
我将刀递给他,他接过刀,看了我一眼,夹杂着嘲笑、轻蔑以及不屑,那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临阵怯战的懦夫,只那一眼,就已令我不寒而栗。我想逃开,但我不敢,我怕某个不经意的举动将他惹恼,他根本就不需要得罪,那条狗就从未得罪他。
这时,它已成了一具尸体,无论它的那条腿因何而断,那渺小身躯的热度都已散去。断裂的骨骼以及关节都将变得僵硬,血液也会流尽,蛆虫会从那个黑洞洞的窟窿里爬出来,爬满整具尸体,臭气将弥漫整个街区,久久无法散去。“唉。”我暗暗地叹了口气。我想,也许它连主人都没有过。
这条狗是一个月前才来到这片街区,那时它的腿还没有断,性情温和,见到人常会远远躲开,靠垃圾桶、臭水沟以及下水道里人类丢弃的食物过活。有时我会远远地看见它趴在街道上晒着太阳,既安静又祥和,那给我的感觉竟不像是一条流浪狗,倒似是与主人短暂分别出来散散步,但没人会理会那些,这里的人连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不知道,他们厌恶流浪狗,恨不得用猎枪将见到的每一条无主人陪伴的狗都射杀掉,那就是一群寄生虫,瘟疫、狂犬病的传播者,除了吠叫,一无是处。
三天前,那条狗的后腿就已经瘸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它见到每个人都会远远地避开,对谁都不会产生威胁,即使只是个五岁的孩子。但也许是地盘之争,或是为了夺得某条母狗,得知道,这地方远不止这一条流浪狗,即便是那些有主人的狗也与流浪狗无异。它们通常凶残、嗜血,哪怕只是一块腐肉,都能引得它们互相撕咬,甚至将对方杀死。这儿的下水道里穿梭着成百条各色流浪狗,而下水道四通八达,几乎能通到这个城市的每一片街区。对于此,我并不惊奇,或许还会有更好的解释,但每次我看到它都会想起它晒太阳的样子,那般宁静,如此不易忘却。但,也就是那时开始,它的性情大变,变得凶狠而又残暴。它不再趴在街道上安然享受它的太阳,而是冲着路人疯狂吠叫,它甚至会随意打翻垃圾桶,将桶内死亡动物的尸体拖到街上,尸体腐烂的臭味顺着风吹满整条街道。就在前一天,我还看见一位清洁工因恼怒而冲它大打出手,而它则直接咬住他手中的扫帚拉扯撕咬,嘴里发出低沉的声音里满是愤怒和不满,如果它的那条后腿完好,它定会跳起来一口咬断那家伙的脖子,将他杀死,像对待那些腐烂的尸体一样拖拉着满大街乱跑。我想,也就是那时候,李萌生了要将它弄死的想法,并且,将会是那般地凶残。
我伸出手来想要摸一摸它,但立刻打消了这一念头。我努力地想要转过头去,却忍不住盯着它的脑袋,盯着它变形的下颌以及那个洞,凝结成死亡的字眼。“从中穿透,”我心里反复念着这样一句话,“从中穿透……从中穿透……从中……”我几乎吐了出来,那里边有一条蠕动着的如白色脑浆般的嗜血虫,它爬了出来,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罪恶感如虫噬般痛苦地涌上心头。这时,我看见了一对眼睛,令我毛骨悚然几乎崩溃的眼神。他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头微微上扬,吐出来的字却离得我那般遥远……
“哼…哼…。”我还没能反应过来,就看见那把刀飞快地劈了下去,接着,一声“咔嚓”伴随着一股腥臭冲我袭来。我看见它的脑袋被砍了下来,一阵拉扯,与身体彻底分开,几条肉丝伴着血在地面滑过,血从切口处涌出,接着,我呕了出来。
我吐得一塌糊涂,而李就仿佛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般疯子似地笑了起来,那声音无时不刻在折磨着我。我的胃一阵抽动,像是被只强劲有力的手一把捏住,酸水伴随着腥臭味顺着食道涌了出来,我想我的胆都破了,胆汁涌进了血管,苦味充斥着整个身体。我感到一阵晕眩,眼泪流了出来,嘴角的唾液又将苦味以及酸味、腥臭味带回到嘴里。我的胃都快要破了,撞击着肺部,全身跟着抽动起来,两腿发软,不住地颤抖。
“接住。”他冲我喊了一句,接着,我感到小腿被狠狠地砸了一下,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散了,骨架正分离瓦解,清空的胃拧缩在了一起,显现从未有过的痛苦。但,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又再次呕吐了出来——是那具无头尸体,包裹在塑料袋里,上半截露在了外边。我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吐了,一阵干呕,胃像是要裂开般的疼痛。我的手插在腰部,我宁可这只手伸进腹部,将胃给拉出来,也不愿意再吐下去,我的胃和肝还有胆,全会吐出来。
我先后吐了三次,才伸出手来捏着袋口将尸体扯进塑料袋里,这让我感觉稍稍好点,但腥臭味依旧强烈。我努力不去想它,却分明感受得到袋子沉重的份量,“尸体”二字冲撞着脑门,只是不想再吐了。我站了起来,伸了伸腰,尽量避开那堆呕吐物。
他又拿来了一个大的袋子,将包裹着尸体的塑料袋装了进去。他用手抓起那颗破碎的头颅,也丢了进去。他将袋口封好,双手抓着将尸体托了起来,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看见他瞪了我一眼,接着,晃了一下脑袋,冲我说,“走。”
接下来的场面我不想再多讲。我也吐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根本就不敢跑开。我跟着他,穿过第九街区,去了江边。江上的风很大,时不时夹杂着尸体腐烂的臭味——酷热使得死物更易腐烂、发臭。他爬上了目所能及最大的那块岩石,用手中那把满是锈迹的刀将无头尸体肢解、分离,接着,将内脏抛进水里。它的肚子空无一物,各个器官干瘪瘪地像是模型,散发出来的腥臭味也叫大风卷裹着吹向远方,那边是工业区,黑压压的灰尘遮住整个天空。他干完手中的活,站了起来,看着远处发了会呆。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满是厌恶,接着,一脚将尸体剩下的部分踢进江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我看见鲜红夹杂着暗黑的血肉在水中漂浮,一会儿浮出,一会儿而又叫微浪翻滚得下沉。
我几乎要哭了出来,但没敢多想。李从岩石上跳了下去,我不知该怎么办,而那具尸体也漂向了远方……
|
|